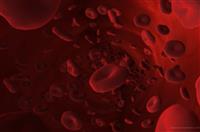欲从太史窥春秋,勿向有字句处求。 ——龚自珍
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 ——冯友兰
大凡思想史、学术史任何一次时风转向,都是由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化合而成的结果:纵向上思想史、学术史内部的推陈出新,横向上相应时期社会变迁造成的外力拉动。纵向矢量与横向矢量的交互作用形成一个力点,这一力点,往往就是某一时代思想史、学术史的定位。如果这一观点大致不错,那么,或许也能同样说明某一时代思想与学术的内部关系?
这种关系大致是三种组合:或者思想重于学术,思想排斥学术;或者学术重于思想,学术排斥思想;或者思想与学术有机结合,相互补足,相互促进。
我私心以为,大陆学界的八十年代属于第一种情况,思想重于学术,尽管有成就,但毕竟是片面成就,并不健康;九十年代按目前趋势发展,则可能出现一个相反的十年——学术重于思想的十年。尽管已经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而且还会继续取得更为可观的学术成就,但是,如果没有思想支撑,单方面的学术成就,毕竟是跛脚成就,同样是不健康的。有鉴于此,王元化先生在他创办的《学术集林》第一辑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希望看到“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这一提法,或许能补救两方面的偏颇。
以上是我的基本想法。至于问题之由来,可能要从余英时先生的一篇讲演词说起。
(一) 如何看待目前对五四的反省
一九八九年,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讲演。大陆中青年学人传阅这篇讲演时间较晚,大约在一九八九年以后,但发生的影响却与日俱增。于此类似,林毓生先生《中国意识形态的危机》也是在一九八九年以前已经译入大陆,但是发生影响也是在一九八九之后。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余英时与林毓生两位先生一个是文化保守主义,一个是政治自由主义,两人师承不同,学术倾向也不同,他们反省五四的出发点与归宿更不同,但是,作为一种外来学理,他们在大陆的传播遭遇却是殊途同归——
首先,他们对五四的批评性反省在大陆一九八九以前不被注意,一九八九以后同时走红;
其次,迄今为止,他们两人之间的学理差异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于此同时,大陆学界的兴趣热点却始终集中在他们在学理形式上的这一相同点——即对于文化传统的保守主义态度。
就我个人阅读的范围而言,林先生著作为大陆知识界某种保守化倾向所用,与林先生师承海耶克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学理相比,出入甚大,两者捏在一起,有点生硬。之所以发生这种局面,多半出于大陆学人的误读,桔过淮则枳。这一点,从他最近一次来沪讲学,再三强调要区分五四精神与五四理念,后者可以反,前者反不得,可以得到佐证。至于余英时先生的遭遇,可能稍微复杂一点,既有误读的地方,也有没误读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认真体会一下他对近代历史传统的保守主义态度与对当下现实的非保守主义态度,这两者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距——在那篇讲演以后他曾经就后一点多次提及甚至多次声明,我们似应该坦率承认,大陆学界一些具有保守主义取向的朋友,还是误读了不少余先生。尤其在他再三声明的那一关节点上,误读出来的那层含义,恐怕是一厢情愿,甚至是南辕北辙。
在这里,为了有助于说明问题,我不得不打一个看上去不伦不类的比喻——余、林二位学理进大陆,有点象当年马克思主义进中国。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为李提摩太第一次介绍进中国,但是并不被当时的知识界注意。后来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才大行其道于中国。不能小看了这个“一声炮响”,它是桔能过淮的必要“物质”条件。一种外来思想能否过河生根,并不是从思想到思想的自繁殖过程,它是需要非思想的“物质”条件的。这种“物质”条件,往往就是类似于这个“一声炮响”的强力,以及这种强力造成的整个知识界对精神读物选择取向的急剧翻转。
余、林两位先生对五四的批评性反省,也是在另一种“一声炮响”之后,在大陆遭到了相同的传播命运:在此之前养在深闺无人识,即时有识,识者亦少;在此之后方才突然走红,形成了不读余、林不能谈五四,不具保守主义学理也不能谈五四,谈了也被人视为肤浅的一时风韵。余、林两位先生对五四的反省,能够受到大陆学界如此欢迎,首先自应归功于两位先生学理独到的客观价值,满足了大陆学界在思想风行十年以后必须补进学术的内部转换需要;其次似也不必讳言,确有另一层非学术因素造成的社会变动之外力拉动。
这后一层因素尽管与学术无关,却又实在重要。它是全面理解九十年代大陆学界何以时风变换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关节点。否认这一层,就如否认前一层学术因素一样,既不公正,也不诚实。否认这一层,就如在一个时空两维世界中抽掉了空间横轴,剩下一个在学术史纯粹时间中单向顺延的一维世界。有没有这样一个一维世界呢?我是很怀疑的。我很赞成这样的提法——要维护学术史的尊严,不过,维护尊严的前提,首先是维护学术史的真实。一个两维坐标,抽掉其中的任何一维,都是不真实的,用来描历史,历史会走形,用来说现实,现实会歪曲。
我觉得,马克思留下的那句话并不陈腐,至今还管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余英时、林毓生文本恰逢其会,实乃大幸——非如此,腾不出一个新的阅读空间,他们对五四的批判性反省,就难以进入大陆思想界。然而又是大不幸——如此一来,学术史上经常见到的对于外来学理的生吞活剥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余、林二位先生以揭示五四一代误读外来学理的历史教训而被大陆学界激赏,然而,揭示误读者本身也逃脱不了被误读的命运。这五年来,是轮到他们自己被误读的激流席卷而去。只是这一次误读,比上一次进步,多了一层“后现代”的味道。调用当下最时髦的解构主义一个语式,叫做:“所指”虚化,“能指”滑动——余、林文本原来有明确规定的“所指”被悄悄虚化了,余、林文本提供的学理“能指”则悄悄滑动起来,而且是向相反方向滑动,最后竟被锁定在一个相反对象上!两位先生海外有知,面对这样一个张冠李戴的局面,恐怕也是啼笑皆非吧?
说得坦率一点,当时那种情况,余、林两先生的外来学理,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一部分朋友内在心理变化的催化剂。对历史事件如五四评价的改变,当然有学术史本身推陈出新的正常发展因素,但是不必讳言,也不是没有另一层因素在起作用——改变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态度,是为了改变对现实状态的评价态度。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才会发生学界中人竟也指鹿为马的误读——一场“能指”与“所指”的背离,甚至是完全反转的可悲误读。我们不是经常批评八十年代对外来学理多半出于误读吗?确实有这种弊病。令人遗憾的是,九十年代同样存在这个被批评的弊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的思想阅读史本身就是从一场误读开始的。
可见,我们需要反省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五四需要反省,八十年代需要反省,九十年代对五四与八十年代的反省本身,也需要反省。
这种反省之反省,可以从林、余两位先生的原初文本开始。余英时的那篇讲演,以及他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其它文章,如“待重头,收拾旧山河”等,或忧思深远,或言简意赅,十分耐读。但是,他过分强调知识分子思潮变迁在本世纪中国社会结构巨变过程中的责任,我私心以为,也是造成上述误读现象的诱发因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的那篇讲演后来收入《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一书,从题目到观点有很大改动。不过,改动后的余英时观点并没有引起注意,原来的文本留在大陆学界的影响,已经成为客观存在,而且至今不衰。出于这一原因,原文本还是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只是以下我所引发的讨论,与其说是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勿宁说是与余英时原文本的大陆读者对话而已。
我的讨论从两个方面进入。一方面是历史事实,一方面是治史方法。前一方面我的基本疑惑大致如下:
第一,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如果暂不作价值判断,仅就事实过程而言,是观念的影响大,还是事变的影响大?
我以为观念打不过事变,事变远大于观念。这个道理就和枪杆子打得过笔杆子一样简单。马克思的名言前面已经引用。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怎么说。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说的是大白话,但是大白话或能化解学术自我扩张形成的思想神话。他说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不是其它。尽管毛泽东在海峡两岸的评价迥然有异,但他毕竟是一个笔杆子来得、枪杆子也来得的人物,恰好还是一个五四思潮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生平又以嗜好历史与善于使用思想先导而出名。作为过来之人,他深知这段历史中的山水沟坎与与利害深浅,由这样一个人来总结这段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中“思变”与“事变”孰轻孰重,或许比我们书生论政更能勘破个中底蕴。
如果觉得上面这句话还不够分量,那么,毛泽东六十年代初接见某日本代表团所说的另一番话,就更应该说明问题了。当时,日本来访者为侵华战争道歉,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说,我还要感谢皇军,没有皇军进来,我还下不了山。此话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但是大陆知识界几乎尽人皆知,是一句相当有分量的话,算不得戏言。
由此,是否可以考虑在反省五四的同时,想一想西安事变呢?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与五四“思变”相比较的历史“事变”,西安事变最为适当。
我以为,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一个张学良,胜过一打陈独秀。
第二,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从五四发源的知识分子左倾化思潮能不能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巨变负责,甚至负责到底?换句话说,有没有这样一列思潮史的直通车,劈开这一路上种种的政治风云、社会动荡、国际变局、乃至军事上的战略决战,从五四的天安门,一直开到十·一的天安门?
我是学思想史的,但我实在不敢奢望,一股政治思潮,两、三群知识分子,四、五种激进报刊,能有如此长驱直入、颠倒乾坤之魔力!知识分子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没有。历史没有这样便宜。在这方面,我倒沾染了一点保守主义态度。
此话可从两头说。
一头是五四激进思潮的始作俑者,如陈独秀、瞿秋白。
陈独秀的作用确实是扭转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为马克思主义进中国铺平了道路。但是他的政治遭遇及晚期思想变化,却不能忽视。我们可以读一读进入四十年代以后他的私人信件,以及这一时期他总结早年思想弄潮与中年政治挫折的其它文字,或许能够体会这一历史隐衷——他能够也必须对五四思潮负责,却不能也无力对以后的政党政治负责。
瞿秋白的思想生命是从在俄国旅行发出《俄乡纪程》开始的。如果没有《俄乡纪程》那样的文学化政治读物,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或许在当时的左倾青年中还产生不了那么大的诗化魅力。中国近代激进思潮有很大一部分动因要归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化历史性格(——在这里,如果依保守主义言路,是可以批评瞿秋白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化历史性格。但是依此言路,五四思潮不也可以“转嫁”一部分责任给新文化运动吗?因为后者文学革命之泽被,已经给前者准备了文学化的社会氛围。这种情况与法国大革命之前整个知识界的文学化十分接近,这一点可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因此,新文化运动并不象目前保守主义者珍视的那样“干净”,它与保守主义者所疾视的五四思潮之间,有一层脱不了的干系)。瞿秋白的政治生命比陈独秀长,陈独秀出局以后,他能够取而代之,延伸入中国共产党上层的路线方针之争,似乎要对政党政治负责了。但是这种政治生命比陈独秀只不过多了三、五年,而且更不能遗忘的是,此后不久,他那种半被己方遗弃半被对方毙杀的政治结局,以及在那种状态下写作的一篇《多余的话》。瞿秋白《多余的话》实在不多余,它触及到思潮史与政治史之间的要害枢纽,是判研观念性影响与政治性实体两者孰轻孰重的珍贵文献。这一文献也许比陈独秀晚年的那些私人信件更能够提示后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作为一种观念力量的政治思潮,起初作用于知识分子,与后来发展为一种思潮政治,变为政治力量出现于政治舞台进入政权角逐,其间有严重差别。
对此,余英时先生在他另一篇文章《陈独秀与中国激进思潮》中有所触及,但是余英时那篇讲演在大陆的读者似乎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想强调的是,
一种政治思潮的代表人物,往往不能代表这种思潮政治,甚至有可能相反,他前期是这种政治思潮的带头羊,后期却是这种思潮政治的替罪羊。从政治思潮到思潮政治,期间必有新的力量出现。这种新的力量对于早期的思潮人物会有一个重新选择的过程,或者是改造性的吸收,或者是把拒绝改造者如陈独秀、难以改造者如瞿秋白,统统排除在外。如果说在政治思潮阶段,越是思想的,方能够越是政治的,思想的力量(责任)大于政治的力量(责任);那么到了思潮政治阶段,情势就倒了过来,越是政治的,方能够越是思想的,政治的力量(责任)大于思想的力量(责任)。
政治思潮的传播阶段,靠的是笔杆子,如果要批评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如余英时所批评的五四激进思潮,只要批评在理,怎么批评都不过分。但是在此之后,政治思潮已经演变为思潮政治,政治力量,甚至是枪杆子——武装起来的政治力量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这时如果还要批评,似乎就不应该继续揪着知识分子揪着思潮观念不放了。否则,就会张冠李戴,不能服人。因此,后人之评价,无论是表彰,还是责难,必须厘清界限,既不能让后期贪揽前期之功,也不能让前期为后期负责。浅白一点说,如果让毛泽东提前承当陈独秀前期传播政治思潮之功,或让陈独秀继续为毛泽东后期思潮政治的结果负责,能够说得过去吗?
这一头是从五四激进思潮内部演变说起,说明政治思潮与思潮政治有联系,但是更有差别,似应仔细区别,不能打统账。另一头,则可以从四十年代中后期大陆再度出现左倾思潮说起,如闻一多、李公朴等一批教授名流,看看这种思潮在中国一再出现,与思潮外部社会因素的横向拉动是否有密切联系。
如果说陈独秀、瞿秋白是从左倾走向右倾,甚至是背叛了左倾——俩人后来在一个时期内皆被恶缢为中共叛徒;那么闻一多与李公朴则提供了一个对位而立的范本——从右倾走向左倾,由激进思潮的反对者变成激进思潮的拥护者,俩人皆为当时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所不容,并为保守主义政权所杀。
闻一多早年留学归来,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在学术上厌恶政治干扰,主张为学术而学术。李公朴不仅早年反激进,甚至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上海清共。这样两个人转变思潮立场,难道是受五四激进思潮影响、纵向顺延下来的吗?抽去一种思潮与具体时间具体空间的联系,恐怕说不通。
如果认为闻一多、李公朴属个人特例,西南联大抗战期间即有左倾之嫌,那么,我可以再让一步,改换一个群体性的例证。如中央大学,如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该校教授集会通过的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其中说到当时的知识分子被迫转向激进抗议的社会性原因:
政府以文化教育为一种政争的工具,即所谓“党化教育”与“思想统治”,这是中外周知无可讳言的事实,……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思想统治”政策——似乎聪明而实愚蠢的政策,因为政府一向对有形的柴米油盐尚且不能控制,何况无形的思想!在经济的束缚和重压下,所得的结果是:迫使文化教育者对政府的极端不满,这种不满的情绪的表现,中央与地方的执政者,统加以左倾为名,以致民意无从宣达,事实上许多人就趋于极端……
〔转引自于进《上海:1949大崩溃》上卷第368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四十年代的那些左倾教授,多半是被学界之外的社会局势所刺激,逼上梁山,而不是受人误导,错上了那列客观上并不存在的从五四开来的直通列车。如果说,五四一代人的激进背景有苏俄布尔什维克因素,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四十年代左倾教授的精神背景,更多的是来自早年在英美所受的民主教育。这一点,实在是耐人寻味。
事实上,类似材料不难寻找。我之所以不避赘累,引出上述文字,无非是说明:在四十年代后期激进思潮与五四早期激进思潮之间,没有直接的逻辑顺延。即使有,也没有从横轴方向上过来的横向拉动作用强大。五四一代中的幸存者、成功者到四十年代已经转入政党政治,后来的激进中人是在反对过这些人为代表的早期激进思潮以后,被横轴方向上发生的社会环境恶化所激荡,重新产生了激进抗议的思潮倾向。能不能抽去两代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抽去两种激进思潮与各自时代的横向联系,仅在激进形式上把两股思潮纵向连缀在一起,说它们之间是纵向的逻辑顺延,而且还要对一九四九年负责呢?我以为不能这么抽,这一抽,怕是要抽去了基本的历史事实。
综合以上两头,我只想说明一个事实:
一种思潮进入某一国家,赢得这一国家激进知识分子的信仰,并且演变为某种政治力量,这是一回事;这一思潮及其政治力量最终能否夺得这一国家的政权,这又是一回事。两者之间不能任意划等号。从思潮滥觞到政权易手,且不说思潮史本身变化多端,千折百回,思潮的观念因素之外,又不知有多少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因素,甚至是国际风云变幻的突发刺激,在此其间冲撞激荡,交汇作用。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思潮进某国,是必然的,甚至这种思潮征服这一国家一部分知识界都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说,这种思潮夺得这一国家的政权也是必然的。
否则,我们怎么理解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马克思主义在其母国可以诞生却不能获胜,在其创始人居住最长时间的英国必然流播,也不能获胜;于此相反,作为一种思潮最后能够席卷政权的地方,为什么是在其创始人最为意外、其思想流播历史最为短暂的俄国与中国?
由此可以思考,在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观念、思潮、文化这些视野之外,是否还有非观念、非思潮、非文化的力量在起作用?后者的力量实在是大得太多太多了。
马克思说,武器的批判胜过批判的武器;列宁说,“战争促成了革命”;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且不论其价值判断,作为事实描述,都是一些道破天机的大实话。实话虽然浅白,却是见道之语,总比一些绕山绕水的学术神话更富有历史信息量。反过来,让某一种观念思潮为某一种政治变局负责,这种说法貌似深刻,追思到底,反可能避免不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这种说法与流行大陆的那种论证某某主义必然胜利、某某主义必然失败的庸俗史观,除了形式对立,在实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以为,无论是为了颂扬还是贬低这种思潮对于该国民族命运的影响,这两种说法,一种是思想史本身自我扩张形成的学术神话,一种是出于功利目的的意识形态,都应该为严肃的历史学家所不取。
以上是就史实讨论,提出两处疑惑,以供商榷,为一个方面。以下另一方面,从史学方法论层面来讨论,则有如下意见——
历史不是思想一家的历史,历史学也不是思想史一家的历史学。思想史的解释是有效的,也是有限的。一个思想史家,既应对本领域解释的有效性有足够的自信,也应该对本领域解释的有限性有充分的自觉。
一部中国现代史,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的沧桑巨变,是需要政治史家、经济史家、社会史家、军事史家、乃至国际关系史家综合回答的问题。其间,思想史家当然可以发言,而且必须发言。但是,每一领域的专家在参与回答这样一个综合问题时,往往容易强调他所研究领域的特定对象在整个综合过程中的作用。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能发生这种偏向:把一个多元多次方程简化成一个一元一次方程,只有一个X,而且这个X多半还是他所研究他能解开的那个X。比如说,让政治史家来回答上述问题,他可能会把这段历史简化成某些政治家的谋略成败史。如果让意识形态专家来解释,那就更加不堪,他会干脆把这段历史简化为某一学说必然胜利另一学说必然失败的证明史。使学者们望而生畏的那些意识形态庸俗史观就是这样出现的。
但是,在学者们对本领域解释范围产生足够的边界意识之前,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讥笑意识形态史学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学者史学观与意识形态史学观不同,甚至得出的结论截然对立,但是学者史学观与意识形态史学观在方法论上却是相通的:都是把历史逻辑化,把历史简化为某一种因素出现以后,就不断向着这一因素所决定或者所负责的方向持续演变,直至一个不可改变的结局最终出现的逻辑过程。他们所不同、所争论的,只是对这个不可改变的最终结局,给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或者欣喜,或者愤怒。
余英时学术著作进大陆,据我所知,严肃的学者普遍持欢迎与接受态度,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感觉他有意识形态色彩。原因何在?有人归因于他特定的政治倾向。我不想如此简单论断。要求一个有具体生活环境的思想家不能有特定的政治倾向,就如要求人走出自己的皮肤一样,这是一种苛求。不能设想,只允许海峡某一边的学者有意识形态立场,不允许另一边的人有其它意识形态立场。有着这种要求,或者不自觉地以这种要求作学术判断的人,不仅是不公正,而且说明他本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已经发展为意识形态的偏见,那就妨碍了学术对话的正常进行。我以为,余英时先生对五四思潮的反省,如果说曾经发生过某种偏差,并不是简单地直接来自意识形态立场。这种偏差,或许是来自一个更深层次,来自历史学家尤其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史家很难避免的一个职业性偏向,即类似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的偏向。
所谓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简略来说,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它能够在纷纭繁杂的历史事实中抽得出一根发展线索,依此排列组合,历史过程将变得符合人类的认识形式,既有价值目的可以发现,又有发展逻辑可以解释;尤其重要的是,历史将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在局部范围内能够认识,因而也就能够把握,能够预测。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对思想史家而言,几乎是一种职业诱惑。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不一定要读黑格尔,才能产生这种倾向,它完全可以自发地产生。甚至可以这样说,越是优秀的思想家,越难摆脱这种诱惑。那种满足于见树不见林的平庸史学家,反而感觉不到这种诱惑。
这是从历史本质主义的客观魅力而言。从思想家主观这一头来说,思维的逻辑性多半是思想家的特有秉赋。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当思想家是以思想史为他的研究对象时,就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中寻找与思维逻辑性相同的东西,即历史的逻辑性。而能够满足历史逻辑性的历史材料又多半是思想史的材料,因为思想史的材料往往最具前后相因的继承性、内在发展的联系性、以及它自身存在形式的逻辑性,同时,还能满足思想家对思想本身的重视。然而,危险往往就潜伏在这里:经过思维逻辑的排列、组合与抽象,是能够出现这样一部思想史的,它能将相应时期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诸多因素象经过磁化的铁屑一样向着一个方向,即思想史的方向排列,以说明观念逻辑一旦出现以后必然经过的路径。不幸的是,到了这种时候,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恐怕只有作者思维逻辑的扩张,没有历史逻辑的延伸,后者很可能是前者的注入与放大了。
被余英时先生批评的五四激进思潮,其深层病根恰恰发生在这里。人类中的少数先知先觉自信能够认识、解释、预测、乃至把握人类历史,而一旦把握了历史,就象传教士摸到了上帝心坎一样,可以按造理性设计,大规模地铲除既成社会,重组新型社会。这种历史本质主义或称历史理性,是西方启蒙时代填补上帝淡出的最大补足物,也是人类所能产生的最大神话——自我神化。正是这一历史理性的乐观发现,才允诺给一部分自信已发现这一秘密的思想家以改造历史、创造历史的权力。在此之下,方有种种大规模破坏传统社会、大规模重建新型社会的自以为是的合法性。这是五四激进思潮之源头,经过二百年在欧亚大陆的流变,到中国近代方形成余英时先生所批判的某种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思潮与黑格尔历史本质主义有精神血缘的联系。近代意识形态如果撇去其下游的庸俗流变,客观承认它在上游源头还有其学理来源的话,那么,它确实是启蒙时代历史理性的一个遥远后裔,黑格尔历史本质主义的一个遥远后裔。
时至今日,经过英美经验主义的长期对峙,以及实证主义的广泛影响,让一般的西方知识界人士承认下列判断可能已不太困难:
人们可以有分门别类的专门史,但不可能有一部前后左右能用逻辑线条拉紧的通史。正如当代哲学家已经习惯说——从本质上说,本来没有本质;当代历史学家也应该乐于承认——从历史上说,从来就没有历史。在此以前,人们认为有历史,只不过是把各种专门史的总和误认为历史,或者干脆说,是把历史编撰学误称为历史。
但在中国,有两个原因,使人们难以产生上述认识。一是中国的文化大传统是以历史学为经度基干三千年一贯的文化传统,以至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别的,而是“史官文化”。这个“史官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要在这样一个“史官文化”中,消解对历史学解释功能的过高估价,极其困难。二是中国近代发育的思想文化新传统中,从法国、德国传沿过来的欧陆历史理性因素,甚于英美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因素。海峡两岸的意识形态,在其初始阶段,都是“以俄为师”,内里却是以法为师、以德为师。这个新传统,更为顽强地妨碍着人们产生上述认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说,我完全赞同余英时先生开创的从五四时代开始反省的思想方向。然而新传统之顽强,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就事论事的平面批判就能解决的。甚至即使将批判延伸至某一学科的学理层面,那种历史理性的思维定势不破除,也未必能彻底解决问题。而且,要消解这个新传统造成的思维定势,也不是某一方的任务,而是需要海峡两岸学界人士的共同反省,共同努力。如果把这种反省与批判限定在某一特定领域,或者限定在特定所指的具体空间,那么这种反省与批判就有可能搁浅,甚至发生这样的尴尬:被批判者的某些思维要素改头换面,又绕回批判者自己身上。如五四一代激进人士,正是因为过高估计思想文化的观念性力量,才接受欧陆历史理性,发生了被余英时批判的激进思潮。但在七十年后,当我们开始对五四思潮的批判时,一旦抽去具体的历史情境,以这一思潮的观念性力量,将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凿空打通,这样的治史方式与思维方式,不也发生了同样的失误吗?从门口扔出去的东西,又从窗口绕回来了。
我的这些商榷意见,相对余英时先生而言,已经是“马后炮”,可能无多大价值,因为他把香港中大那篇讲演收进集子时,已作了很大改动。不过相对那篇讲演在大陆的诸多读者朋友而言,可能还未过时,故而不揣累赘,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持不同意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