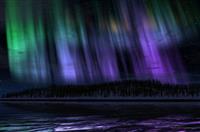摘要: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以前圣与王合一、道统与政统合一;春秋战国以降,圣与王一分而为二,道统与政统分立。道与教的关系:道是本根,教是枝叶;道是本质,教是形式;道是源,教是流。儒家道统思想源远流长,教统亦渊源甚古,二者的关系:道统是教统价值之源和指导思想,教统是道统落实的基本途径。三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秦汉以降政教时有矛盾冲突。在儒家中国语境下讨论政教关系问题不能忽视道统这一维度,应该在道统统摄政统与教统的三元结构下探讨政教关系的特征。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ina before the sage and the emperor be made one, orthodoxy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drop, the sage and the emperor divided in two, orthodoxy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separation. The relation Tao and Jiao: Tao is the root, the essence , the source , Jiao is the leaves and branches,the form,the flow. Confucian orthodoxy is well-established,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is also very ancient orig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rthodoxy is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source of value and the guiding ideology,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is a basic way of implement of orthodoxy. The Three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affairs and the education, the official and the teachers is not divided,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when there is a conflict. In the Confucian China context discussed the politics and education relationship not ignored orthodoxy this dimension, should be to overto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three element structure system of characteristic.
Keywords: Chinese; Confucian orthodoxy;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political system; politics and politics and politics and education relationship
一、“政教关系”的一般理论
所谓“政教关系”(Church-State Relations)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很早就有讨论,一般是指现代国家(政府)与宗教团体(教会)的基本关系。黑格尔曾经从国家与教会的联系中理解“政教关系”的含义:“宗教如果是真实的宗教,就不会对国家采取否定和论战的方向,而会承认国家并予以支持;此外它还具有独立的地位和表现。它的教化事业在于仪式和教义,为此他需要地产和财产,同样也需要为教会服务的人,因此就发生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规定是简单的。依据事物的本性,国家应全力支持和保护教会使其达成宗教目的,这在它乃是履行一种义务;又因为宗教是在人的内心深处保证国家完整统一的因素,所以国家更应要求它的所有公民都加入教会,因为其内容既然是与观念的深处相关,所以不是国家所能干预的。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从而是个强国,在这方面可以表示更宽大些,对触及国家的一切细枝末节可以完全不问,甚至可以容忍那些根据宗教理由而竟不承认对国家负有直接义务的教会(当然这要看数量而定);这是因为国家已把这些教会成员交给市民社会使其受规律的约束,国家自己就满足于他们用消极的办法(好比用交换或代替的办法)来完成对它的直接义务”。[①]《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从教会与国家角度理解“政教关系”,认为:“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做是一种体制现象,然而,从根本性的观点出发,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存在于人类之中精神或内心生活与社会或集体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②]。中国有学者从宗教与政府的关系角度概括政教关系有以下4种模式:1、政教合一。宗教领袖可以兼国家首脑,在制定国家内外政策上拥有最高权威,国家把宗教教义与法典奉为所有活动的准则。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受宗教指导。政教同体,其他宗教是非法的。2、政教分离。国家不支持、禁止和歧视任何宗教。国家不征收宗教税,也不向宗教组织提供任何形式的财政支持。政府不设宗教事务机构,也不干预宗教组织的事务。宗教组织不受政府的政治领导,也不能干预国家的司法、行政和教育。政教关系完全由法律调节。3、国教。国家承认某一宗教或教派为正统信仰及独尊地位,国家为宗教提供法律上的特权和财政上的支持。4、国家指导宗教。宗教接受国家的政治领导和政治方针,国家承认宗教。国家行政部门管理宗教组织,宗教不介入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③]张践教授突破把政教关系仅仅视为国家政权与教会组织之间关系的流行的狭义理解,全面论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揭示政治的三重结构:政治权力、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论述宗教对三者的作用,形成广义的政教关系论。作者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政教关系进行类型分析,概括出四种类型:政教一体型的神权政治、政教依赖型的神学政治、政教主从型的神辅政治、政教独立型的法制政治。”[④]也有学者从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出发,认为“所谓政教关系,一般指的是特定的政权与存在其治下的宗教之间的各种关系。它包括宗教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位置;特定的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位置;特定的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影响力,以及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介入程度等方面。具体的表现涉及宗教团体的自主权的大小;宗教团体及宗教领导人影响政治和参与公共决策的程度等。”[⑤]更有学者对政教关系含义进行更细致的区分,“政教关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政教关系主要包括三对不同层次上的关系,即“第一,意识形态层次上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二,权力主体层次上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三,社会事务层次上的宗教社会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狭义上的政教关系“主要指宗教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多的属于实践层次上的关系,但在立论上则要同深层次的关系即教会与国家关系相关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本质上,要取决于教会与国家双方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⑥]。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⑦],涵括了政府与宗教、政府与教会、宗教与政治及教会与政治四种度向。[⑧]总之,在东西方历史上,政教关系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由于政治、经济背景不同,东西方政教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很大差异。
二、儒家中国道、教、政视野下的政教关系问题
(一)道与政、道统与政统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道与政、道统与政统呈现出亦分亦合,不即不离,一虚一实,相反相成,互为作用的特点。以时间而言,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是道统与政统合一的,“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⑨];以人物而言,孔子以前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与王一体的,是道统与政统合一的人格体现。“这些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既是普天之下的思想导师,也是各个时代最高的政治领袖,是实践政治的操作者,履行着最高的政治责任。这些人一身兼二任,游刃有余地主宰着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政治两大领域。”[⑩]春秋战国以降,在现实中圣与王分而为二,道学在师儒,权势在帝王,儒家只好寻求在圣与王分而为二情况下圣怎么制约王,于是孔子由高扬“道统”意识,以与君主所代表的“政统”形成两个相涉而又分立的系统。从此以后,政统与道统不再合一,道统之中不再有历代帝王的地位,而政统中的历代帝王则要接受道统的指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这就使得他们既有别于以色列先知的直接诉诸普遍性、超越性的上帝,也不同于希腊哲人对自然秩序的探索。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和政治权威发生了面对面的关系。但是以现实的势力而言,知识分子和各国君主是绝对无从相提并论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尊重,基本上是由于他们代表了道。建筑在赤裸裸暴力基础上的势是不可能有号召力的,政权多少都要具备某种合法性。这一点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权都必须遵守的通则。中国的道也正在这一点上显出它的特殊之处。”[11]“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12]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既有和谐统一的一面,又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和对立,代表价值理性的道统、师儒与代表工具理性的政统、王侯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道统与政统的一般关系是道统高于政统、涵摄政统,二者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在儒家看来,“道统”的核心是道德标准与精神价值,由伏羲尧舜孔子等古圣人创立,由民间历代圣贤大儒代表并传承,是衡量社会政治的最高价值标准,是评判国家政府的独立精神力量,而“政统”则由皇帝或政府承担与代表,只表明皇帝或政府具有世俗权力的合法性,而不具有精神权力的合法性,即不具有“道统”上的合法性。在“道统”与“政统”分离的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一个皇帝敢说自己代表“道统”(社会道德精神上的合法性),因为皇帝知道,“道统”自古以来都由尧舜孔孟及民间大儒代表,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只代表“政统”(政治权力承接与使用上的合法性)。因此,他们不但不敢与圣贤争“道统”,反而降尊卑怀诚心尊重“道统”,敬畏“道统”,愿意接受“道统”的评判监督。这表现在朝廷礼仪上,皇帝与一切政府官员进孔庙与国子监要下马,皇帝祭孔子也要像祭天一样行三跪九叩大礼。因此,在中国政治传统中,“道统”高于“政统”,“道统”不仅是“政统”的评价标准与道德合法性的来源,也是社会普遍道德与精神价值的基础与来源。也就是说,“道统”不仅承担着批评监督“政统”的功能,还承担着建设与维系社会普遍道德与精神价值的功能。……从中国文化中“道统”和“政统”的关系以及中国国家的宗教性质来看,中国的政治是政教既分离又合一的政治[13]。
(二)道与教、道统与教统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深含在“道”这个概念当中,“道”本意是指地上人行之道。古代思想家们把它引申、抽象为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最一般性法则,有“天道”、“人道”、“地道”之别。不仅道家,儒家也讲“道”,且十分重视“道”,其重视程度不亚于道家。古今中外,圣贤仙佛,各教教主悟道所形成的教本是同根于一道,但由于应各地风土、民情、语言、习惯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兴起许多不同修道方代的宗教派别,形成了今天多元宗教的格局。儒家对“道”与“教”关系的讨论以《中庸》“修道谓之教”为典型。郑玄注《中庸》“修道谓之教”:“修,治也。治而广之,人放效之,是曰教。”孔颖达疏曰:“修道之谓教”,谓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于下,是“修道之谓教”也。在郑玄、孔颖达看来,人之本性源自于天,循性而有人道,人(君)修治、修行此道而教化百姓。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朱熹《中庸或问》在对“修道之谓教”作进一步解说中指出:“修道之谓教,言圣人因是道而品节之,以立法垂训于天下,是则所谓教也。盖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虽得其形气之正,然其清浊厚薄之禀,亦有不能不异者,是以贤智者或失之过,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于此者,亦或不能无失于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间,而于所谓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错杂,而无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则于所谓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无以适乎所行之宜。惟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天理浑然,无所亏阙,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为之品节防范,以立教于天下,使夫过不及者,有以取中焉。”在朱熹看来,“修道之谓教”是指人与物由于气禀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不免有所昏蔽错杂,而无以全其所受之正”,因此有可能背“道”而行;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天理浑然,无所亏阙,故能依据“道”而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立礼、乐、刑、政之属,以教化天下。在朱熹这里,“修道之谓教”中的“修道”,不是郑玄、孔颖达的修治或修行“道”,而是指圣人依据“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体现为礼、乐、刑、政等。
明代王阳明对朱子的解说不以为然,他自己有不同的解说。《传习录》上卷127条,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属。此意如何”?先生(王阳明)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要圣人品节?却是不完全的对象。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说,下面由教入道的,缘何舍了圣人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工夫?却是圣人之敢为虚设矣”。子莘请问。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从本原上说。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修道则贤知者不得而过,愚不肯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此‘教’字与‘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与‘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王阳明认为朱子的说法不合子思本意,没有办法解释一般人戒慎恐惧,由教入道,下学上达的修养功夫。他认为子思性、道、教都是从本原上说的,修道而学,此道便是教,这就是《中庸》“自明诚,谓之教”。人们只要能够循道而行,这个“道”便是教,就像天地阴阳、四时八节、风雨霜露,都是“教”。人通过修道的功夫复其性之本体,像圣人那样率性之道,就是“修道之谓教”。显然,他不同意朱熹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品节人、物,立法垂训的“教”,试图回归子思由内而外,自下而上,中和位育,尽性至命,达到尽人合天,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比较起来,在道与教之间,朱熹似乎更侧重自上而下垂教,阳明似乎更侧重自下而上修道。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说:“《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言身之所行,举凡日用事为,其大经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称‘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中庸所言‘修道之谓教’也。”[14]是说《中庸》所言之道就是人伦之道,处理好人伦关系就是修道,就是教化。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历代对“修道之谓教”虽然有不仅相同的理解,但大致都是说所谓“修道”指的是修学圣人之道,而圣人之道是以人伦为主体的人道;“教”是说这是一种教化过程:对他人而言是教化、教育,对自己而言是自修、自证。《中庸》将人们的这种对圣人之道的修学称为“教”,可见此时的“教”是同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一致的。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但也有宗教的蕴涵,就是儒教之“教”的基本含义。儒家讲修道之教,这不是佛家道家离世孤修的纯粹生命修炼,而是儒家经过自我修养(修己)基础上安人、修己安百姓、正己正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在“教统”上的体现。
对于道与教的关系,现代民间大儒段正元对道与教进行了分疏,认为“道”一而“教”殊,古来是“一本”(道)散为“万殊”(各种宗教),将来要“万殊”仍归“一本”。段正元在《道德约言》中说:“教犹植物之花,道犹植物之本。花由本生,教由道发,花不能离本而生,教不能离道而存。花不能与根本比美丑,教不能与道较高下。道本千变万化,圆通无碍。教则单取一线,有一定不移之方针。”《大成礼拜杂志》第五十九礼拜:“教皆道之用,教愈合而道愈完。”道与教的关系上,段正元显然认为道是教的价值之源,教是道的工具承担。道是本根,教是枝叶;道是本质,教是形式;道是源,教是流。教之兴起是为了传道、明道、弘道、行道。正因为这样,段正元强调信教须知重道。他说,各教在大道失传后兴盛起来,原本也是益于世道人心的,可是各教后来的信仰者则各怀排他之心,造成了教派之间、教派内部的争执,甚至引发宗教战争和残杀,这样就失去了教祖原先立教的本旨。他揭示万教的原理就是大道,道一而教不同。要协调万教,就要明道,返回大道,这是解决当今多元宗教竞争而导致人类的各种灾难的唯一途径。只要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以道为归宿,则宗教争斗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儒家道统,即指儒家圣人之道发展演变的系统,它包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祥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伟人、先哲和儒家圣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董仲舒、王充、韩愈、程、朱、陆、王等所承传之道及道的精神、传道的统绪。儒家道统思想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神圣,再下来就是尧、舜、禹、文、武、周公这些古代圣王。
孔子继承文王仁政和周公周礼,把礼乐文化观念化,对当时读书相礼的儒者进行了改造,提升他们的品质,揭示礼乐文化精神内涵和人性本质,同时欲以礼乐来平治天下,创立了儒家学派,为道统的传授和推广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由此确立了他在道统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后世以周孔之道并称。孟子更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数至孔子,清晰地勾勒出一幅自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圣人之道相传授受统绪,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并为后世所遵循。真正对道统有系统表述的是唐代中期的韩愈。他吸取了佛教祖统说的思想资料,构建了一个儒家的道统传承谱系。他著《原道》一文,标志了道统论的正式提出。认为,“先王之道”从尧开其“端”,一直传到孔孟,从不间断:“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5]虽然从一开始九对荀子有所微词,以至于道了宋儒把荀子干脆排斥与道统之外,但荀子在道统史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他继承发展孔子的思想,又吸收改造道家的思想,提出“天有常道”的命题,强调天道自然,人道有为。其法先王、发后王的意识实质上是贯彻在他的文化生命中的一种历史文化精神,也就是承接道统的意识。
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16]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使儒家“道统”进入政治领域。隋代王通在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形势下有志于恢复先王之道,主张以儒学为主,三教可一,即三教可以融合的观点。受韩愈道统说的影响,儒学发展至理学,道统意识犹为凸显。
北宋程颐把其兄程颢尊为道统传人,他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17]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道统论是指圣贤一脉相传的“十六字箴言”。他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18]陆九渊继承孟氏而注重道德,他从孟子关于“心”的思想中所吸取的也正是儒家道德学说,以儒家的道德为道统之“道”。王阳明虽然以“致良知”取代道统论,但仍然以“十六字箴言”作为心学之源。他还说道:“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宋儒否定韩愈在道统中的地位,“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宋史·朱熹传》)。
儒家的教统渊源甚古,至少尧舜时代已经有了五伦之教,《孟子·滕文公上》:“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至西周应该已经很普遍了,《周礼》中,大司徒的职责中有所谓的“十二教”:“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其教民的内容可谓具体而广泛,涉及民生的各个层面。春秋时代孔子以“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感,抢救并整理了濒临散失危险的上古文化典籍,同时,以此为教本,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从而打破了教在官方的独霸局面,使学校教育、社会教化融为一体。由孔子开创的儒学其教的内容就是价值理性的“仁义道德”,而其手段则是诗书礼乐。儒家之“教”即通过宣讲、表彰、学校教育以及各种祭祀仪式等方式,向人们灌注儒家价值观念,使其遵守社会秩序。儒家还非常重视礼乐文化中的祭祀传统,形成了“神道设教”的传统。概括地说,教统是古圣以道化人、化世的“教化、教育、宗教之传统”,这些在历史上是不分的,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西方分析的思维习惯,故不得不分而言之。
传统上的“教统”的展开就是由孔子开创的“六艺之教”,即礼教、乐教、诗教、书教、易教、春秋教。《礼记·经解》中引孔子一段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马一浮据以将中国一切学术分判为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六类学术(六艺之教);“六艺之教,通天地,亘古今,而莫能外也。
六艺之人,无圣凡,无贤否,而莫能出也。散为万事,合为—理。此判教之大略也。”[19]六艺之教范围天地古今一切学术而不遗,可以说是教统的全面展现。
儒家道统与教统的关系是在儒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道统”是“教统”价值之源和指导思想,“教统”是“道统”落实的基本途径。
(三)政与教、政统与教统的关系
要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首先必要弄清楚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的“政”、“教”内涵。《说文》:“政,正也。”《墨子·天志上》:“且夫义者政也[20],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这里“政”一般释为“正”,《论语·子路篇》: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论语·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说季康子向孔子问政治。孔子答道:“‘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你自己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说明古代政与正可以互训。政治的核心价值一个“正”字就可以概括。这就言简义赅地阐明正直、公正的为政理念和为官之道。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说文》)“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虽有狭义的宗教含义,但还更主要的是教育和教化的含义[21]。所以,中国古代“政”、“教”的本意是指在上者以其道德楷模以身作则,上行下效,寓教于治,实现政治的良好治理。孔子曰:“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德行就就象风,老百姓的德行就象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会随着风而俯倒。”孔子是在强调为政者的德行很重要,对下面的民众有决定性的影响。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者的德行不好,上行下效,老百姓就不可能一心向善,整个社会就会道德滑坡。《孟子·藤文公上》孟子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意思是说在上位的人有什么喜好,下面的人一定就会喜好得更厉害。为政者的德行是风,老百姓的德行是草。草受风吹,必然随风倒。由“政”与“教”合成的“政教”一词在中国古代则指政治与教化。《逸周书·本典》:“今朕不知明德所则,政教所行。”《管子·法法》又说:“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国家之兴亡系于政教的得失。《荀子·王制》:“本政教,正法则”《荀子·大略》):“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内脩政教,外应诸侯。”
关于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很多学者认为是“政教合一”,其实不能简单地用流行的政教合一模式套,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只是一种类似的政教合一。
三代政教、官师不分,这本已是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海外学者如张光直、徐复观等,国内老一辈学者如杨向奎等,近年来学者如谢维扬、陈来、陈明等都持此说。《礼记·王制》中亦云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陈澔在这一节下注云:“此乡学教民取士之法也,而大司徒则总其政令者也。”可见,当时的政治就是教化,教化就是政治,二者难分难解,浑然一体。章学诚认为,三代之世,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圣人因事立教,寓教于政,他写道:“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文史通义·原道中》)在官学的一统天下里,所学者,不外修齐治平之道,教化即政治;所师者,皆为守官典法之人,官吏即师傅,政教官师一体。
及至春秋,王官失于野,学术下私人,道术为天下裂,私学勃兴,诸子蜂出,百家争鸣,三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局面在春秋又被打破了,于是出现了《庄子·天下》篇中所谓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道术之分裂,乃是道统、政统、学统、教统的分裂,各家各派皆“思以其道易天下”,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于是,“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上》)随着道术散乱、学术下移,教育、教化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政府的官吏不再承担师的职能,这一职能逐渐被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士(知识分子)阶层所取代,政统与道统、王权与教权发生了分裂。但这种分裂只是暂时的。战国之世,各国君主尊师礼贤,目的显然是想获得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道义力量的支持;而诸子奔走列国、游说王侯,也无非是期望借重王侯的政治力量以推行其道。比及秦统一六国,焚禁《诗》《书》,坑杀儒生,“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也是想重建官师治教合一的格局,但由于只用法家思想,排斥别家,甚至“焚书坑儒”,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秦汉以后,政教结合及其内在冲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汉代独尊儒术,以经学为意识形态的主体,以师儒为吏,即循吏;皇权与教权结合,实现了官师政教的统一,但是由于政统和道统的价值关怀并不完全一致,皇权压制道统权威,打击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知识分子则以道统权威抗衡皇权,两者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因此,要准确地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还必须考察政统与教统之上的道统,注意到他们形成了一种三元结构:
所以,在儒家中国语境下讨论政教关系问题不能忽视道统这一维度,应该在道统统摄政统与教统的三元结构下探讨政教关系的特征。通过对历史上政教关系演变的初步考察,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特征:
1、治民之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礼记·学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古圣先王把教育作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这是很高的治国智慧。根据《尚书》的记载,早在尧帝的时代,便让舜担任司徒(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一职,主管百姓教育,以“五典”(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教育民众。在舜的时代,则由契担任司徒,推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孟子》上说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汉书·礼乐志》说:“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古代的君王,没有不把教化看作是大事的。他们设立大学以教化于国都,设立庠序以教化于城镇乡村。可见,自尧舜之时起,古圣先王就把立学校,行教化放在治国平天下的优先位置,正如后来《盐铁论》概括说:“故治民之道,务笃于教也。” 于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成为中国古代优秀的政治传统一直持续了下来,使得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而没有衰亡。
2、以道统合政教:寓治于教,寓教于治
儒家传统以上强调以道统合政教,穷则为儒家隐者,“寓治于教”,达则为士大夫,“寓教于治”,就成为儒者人生和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荀子·儒效》认为一个儒者应该:“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政”就是入仕参政,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美俗”就是隐退民间,修身养性,以身作则,教化社会,化民成俗。贾谊《新书·大政下》后来更有总结性的概括: “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民为国之本,如何治国理民?有道然后教,有教然后老百姓得以教化,国家得以治理。
3、政教一定张力下的平衡:不即不离,相维相济
政治与宗教的都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但独自的特性。宗教会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和稳定性的资源,表现出特殊的超越性、神圣性和教化功能来发挥其社会整合作用。政权也会通过允许宗教的适度发展以发挥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但总是要高于教权,要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不会让你凌驾于政治之上。这是中国政教关系的基本状况。至于儒家,杨阳解释说:“儒家将现实社会和政治秩序内化为人本质,在其超越性理想与现实社会及王权之间建立了相互融通的关系,不仅将社会个体理想实践的过程完全落实为对王权政治的参与,而且还将其生命活动的意义圈定在与王权合作的范围内。”[22]我同意他这段话的前半句,不认同他的后半句。儒家确实在其超越性理想与现实社会及王权之间建立了相互融通的关系,但并没有将社会个体理想实践的过程完全落实为对王权政治的参与,更没有还将其生命活动的意义圈定在与王权合作的范围内。毋庸讳言,历史上是有杨阳所说的儒者,但决不是儒家的主流,也不能代表儒家的主导倾向。儒者和帝王都明白政与教各有特性,所长,各有所短,儒者把握道统,教化社会,皇帝接受道统,支持儒生,有点儿类似西方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但西方是二元分离,中国则是二元和合。
4、儒者凭道立教,具有公众知识分子与僧侣的双重性
儒家凭道立教,以经学为学术基础,以圣贤为理想人格,确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立民族信仰体系,为社会制定伦理道德规范,通过教育、教化活动重建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正如余英时所说,“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自始即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他们管恺撒的事这一点来说,他们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就他们代表‘道’而言,则他们又接近西方的僧侣和神学家。”[23]儒者就他们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参与而言类似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们还有一般自由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道统和为护卫道统的宗教精神,这则是西方宗教家所具有的。儒家主体的思想和实践模式是内圣外王之道,儒生们通过内圣的修养,有宗教性的体验,然后他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就会带着一种超功利的宗教式的热情和布道精神,但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一种狂热的宗教行为,而是履行人伦道德的形式,是做人和成圣的必由之路。
5、儒家以人文理性为本质特征,以儒为主,整合多元宗教
儒家思想体系以人文理性为主,体现为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等核心价值观,使儒家在历史上可以与外来的各种思想文化交流融会,正如《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故可以包容土生土长的、外来的各种文化成分,只要不使自身发生质变,都能心胸开阔,兼收并蓄,百川归海,不择细流。因为能开放,能包容,就能够融会贯通。在对待其他宗教方面,因为儒家有宗教这一层面的内容,这就使儒家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发挥教育和教化功能,也发挥了宗教信仰的功能,所以在历史上儒家也一定程度上担当也满足了儒生、士大夫精神信仰需求,更重要的是在宗教信仰层面面对多元宗教,可以与别的宗教进行对话,进行交流,以儒为主,整合多元宗教(当然也不乏冲突)。而以人文理性为主,具有复合形态的儒家或儒教就高于其他单一的宗教与世俗哲学、伦理,形成“圆教”[24],没有排他性,可以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历史上三教合流,有儒家式道教徒、儒家式佛教徒,现在世界上如美国也有儒家基督徒,在东南亚已经有儒家式伊斯兰教徒,儒家式印度教徒等。这对于其他单一型的宗教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由于儒家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性活动始终是围绕人事展开的,可以说是人道教或人文教。中国古代大多数哲学家有信仰,但对宗教都不会迷狂,他们所关心的乃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
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以人文理性为主、以宗教为辅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没有宗教偏见,没有宗教狂热,没有宗教战争,使得各种宗教传进中国后,争斗锋芒都被磨钝,进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中国文化成为各种宗教的大熔炉,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程就就是典型例子。
《学术界》2014年第6期,P164-175,1.3万字。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年 ,第 273 页。
[②] [英]戴维·米勒 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等组织翻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 ,第 108 页。
[③] 刘澎:《中国的政教关系:特点及发展趋势》,刘澎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2014-02-04。
[④]张践:《论政教关系的层次与类型》,《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⑤]何其敏:《论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 年第 4 期,第 12 页。
[⑥]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2002 年,第 3 页。
[⑦]何光沪:《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儒教问题争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
[⑧]理论组:《政教分离:误解与厘清》,基督徒香港守望社:《过渡期的香港:政治、经济、社会》(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8),页96
[⑨]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
[⑩]喻中:《历史上的道统与政统》,《法制日报》,2009年04月01日。
[1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1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
[13]蒋庆:《儒家的生命之道与政教传统——谈儒家的心性学统、道统与政统》,www.confucius2000.com
[14]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第43页。
[15] 韩愈:《原道》。
[16] 董仲舒:《贤良对策三》。
[17]《明道先生墓表》,《伊川文集》卷七
[18] 《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
[19]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51页。
[20]《墨子闲估》卷七:王云:“‘政 ’与‘正’同,下篇皆作‘正’。”诒让案:意林引下篇,“正”皆作“政”,二字互通。“义者正也”,言义者所以正治人也。
[21]韩星:《儒家教统:教化、教育与宗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3日。
[22]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8页。
[23]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
[24]当代新儒家中,有专论及于圆教者,有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诸,而尤以牟先生开发最多,详见王财贵《新儒家圆教理论之特殊性新儒家圆教理论之特殊性》,《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之二》,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12月,第4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