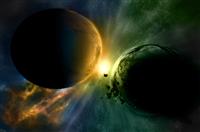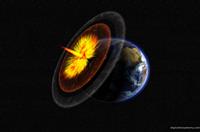随着保守党赢得英国大选,与此结果相捆绑的“退欧”公投也成为新一届英国政府优先的政治议程。英国国内各政治派别、英国与欧盟机构以及其他成员国之间,都将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政治博弈。对于研究欧洲问题的中国学者而言,这既是一个分析英国内政外交和社情民意的绝好案例,也可以借此深入观察其对欧洲一体化未来方向的影响。由于英国“退欧”问题的复杂性,观察者应当以问题导向建立起多重视角。
首先是通过英国政党政治变化进行观察的视角,包括保守党内部斗争、保守党与工党的传统博弈、独立党与苏格兰民族党崛起等政党政治现象。卡梅伦首相在2013年1月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发表的正式讲话,是“退欧”问题成为政治议程的标志,这是执政的保守党内部斗争激化、卡梅伦对此掌控乏力的结果。尽管“疑欧”势力在保守党内有深厚传统,而且自欧债危机以来更有上升之势,但被视为“亲欧派”的卡梅伦成为了“退欧”公投的“推手”,表明其已难以掌控党内形势。因此,将党内纷争公开化并将其与大选相捆绑,保住其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并领导保守党获胜,成为卡梅伦的首要政治目标。从历史上看,与欧盟关系始终是保守党内部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稍有不慎,即便强势者如撒切尔夫人也会因此折戟于党内斗争。因此,卡梅伦以承诺“退欧公投”向党内“疑欧派”做出妥协。在换取党内团结、稳固地位并赢得选战后,再全力应对“退欧”问题,这在保守党内“疑欧”势大的情况下,不失为超脱于“挺欧”派与“疑欧”派争斗之上、以退为进、固守待机的政治高招。
同时,保守党内“疑欧”势大以及卡梅伦的“退让”更与英国政党政治的生态变化密切相关。尽管大选台面上仍然是保守党对阵工党的传统戏码,但独立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以及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崛起,以及随着苏格兰独立公投而成功“上位”的苏格兰民族党,正改造着英国的政治生态,与欧盟关系问题各党都无法回避并成为变化的焦点。无论我们从外部来看,英国“退欧”是多么的“不合情理”,民意是如何地被政党、选举所“操弄”,但近年来将“疑欧”甚至“反欧”作为“捍卫国家利益”利器的观点,在英国民意中渐成主流,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英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政党及其领导人对此持何种立场,只能因势利导、顺风使舵,否则就会吃苦头,自民党的衰落和工党在苏格兰的传统地盘被侵吞,都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接下来从这个视角来观察“退欧”问题的走向也很有意思:卡梅伦所倚重的黑格弃外交大臣而转任保守党下院领袖,其职位由被视为“疑欧”人物的哈蒙德接任,这既能让卡梅伦更好地掌控下院尤其是本党内部的动向,又能以重要阁员位置安抚“疑欧”人士,同时还能让哈蒙德作为“欧盟改革”问题的关键谈判人在实践中“受教育”。此外,大选结果证明,卡梅伦的“退欧”公投策略取得初步成功:工党落败并被“挺欧”的苏格兰民族党所蚕食,独立党至少没有在议席上捞到好处,当前政党格局对其推进“退欧”公投有利。如果卡梅伦是货真价实的“挺欧”派,即便民意走向仍不利,苏格兰民族党“退欧则脱英”的威胁也可能作为最后的杀手锏,被用来阻止英国“退欧”成为现实。
其次是英国乃至欧洲民主、民粹政治嬗变的视角,包括“公投”的权威性与不确定性、媒体的政治权力以及民粹政治的泛欧洲化。政治参与频繁诉诸“公投”的形式,成为近年来英国乃至欧洲政坛的“新常态”。作为“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和修正形式”的“公投”,如此频繁地成为政治决策的主角,至少传递出两个信息:其一是政治生活中对国家前途和命运产生重要影响、关乎大多数人利益的重大问题集中出现?需要靠“公投”这种直接民主形式来寻求共识、迅速决断;其二是现有的代议制民主在这些问题上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某种质疑?不得不在重大问题上寻求“公投”这种直接的民意表达来加以“修正和补充”。
回到英国的政治实践,在自1973年以来英国政府进行的12次公投中,全国性的公投只有2次,即1975年工党威尔逊政府时期有关英国在欧共体中地位的公投以及2011年有关选举制度改革的公投。其中1975年公投的背景、命题等与此次“退欧”公投具有相似性,但其政治环境和政治操作的复杂性则有不同。由于公投在政治实践中优劣势并存,具体到此次“退欧”公投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包括:第一,由于公投结果具有无可替代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无论此次公投结果如何,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英国与欧盟的紧张关系在政策层面可能得以暂时缓解,但其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极有可能如同苏格兰独立问题一样在将来仍以诉诸公投的形式卷土重来;第二,公投可以控制肆意立法、避免“民意扭曲”,但由于其回避了民主协商环节,简单多数的决议形成程序可能非但无助于“达成共识”,反而可能激化对立,甚至造成英国社会的分裂;第三,由于全民素质、自身利益以及对问题关注度的差异,公投结果是否能在“退欧”问题上确保英国利益的最大化存疑,“民主”与政策有效性之间的鸿沟可能扩大;第四,同样由于上述差异,媒体在公投前后将扮演极其重要的政治角色,媒体在英国乃至欧洲借公投成为重要政治力量的趋势明显。
公投现象折射出来的是,民主与民粹政治之间的界限在当前英国和欧洲政治实践中模糊难辨,而且民粹正借公投这一形式成为泛欧洲的政治势力。政府力量的弱化以及政治权力向媒体、网络以及特定诉求人群的转移,导致公投在成为民主的“有益补充”之前,就有被作为民粹诉求工具的可能。同时,一体化成为各国民粹势力的“共同靶子”,疑欧、反欧乃至退欧成为民粹势力的核心议题,也是其成为泛欧洲化现象的动力。英国“退欧”公投是为本国乃至欧洲民粹势力上升画上句号还是就此制造出更多的“麻烦”,值得我们认真观察。
最后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与欧盟博弈的视角,包括“疑欧”派的“维权”诉求是否能成功转换成卡梅伦政府的“改革”诉求?欧盟内部有多少英国的“盟友”?“法德轴心”和欧盟机构如何应对?以及“双速欧洲”是否将导致欧元区与非欧元区两个平行权力中心的出现?卡梅伦政府正试图将“退欧”议题转换为要求欧盟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产业政策以及移民等核心问题上做出相应改革的诉求,并携此展开了数轮欧陆“游说之旅”。当前欧盟内部尤其是欧元区内部的紧缩与反紧缩之争、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国家在“过度管制”以及一体化加速等问题上的分歧,的确为英国政府的“改革”诉求提供了环境,如果运用得当,近期被重点关注的移民问题也有可能成为英国要求欧盟“改革”的抓手。如果英国能借此在欧盟内部找到更多盟友,则其与欧盟的谈判筹码就会增加。但卡梅伦政府必须把握好就“改革”展开游说和进行谈判的度,必须在不对欧盟过度施压的同时,适当降低国内民众尤其是“疑欧”派的期望值。一旦其要价过高,或是在欧盟内部寻找“盟友”的努力被法德和欧盟机构视为“拆台”,就可能招致欧盟和法德的强硬立场,并在国内“疑欧”派与欧盟之间形成尖锐对立,最终将自己逼到“非退不可”的尴尬境地。同时,对于将“退欧”与“维权”牢牢捆绑在一起的英国民众和保守党内“疑欧”势力来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收议题转换以及英国与欧盟的谈判结果,都需要持续观察。
想得更远一些,以英国“退欧”公投为名来施压欧盟“改革”的,是认为“一体化走得太远”的国家主权论者或者“唯单一市场论者”,但目前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出现的一体化加速和拓展之势,尤其是欧元区的进一步整合,对于英国这样的非欧元区国家产生的外溢效应,是刺激英国疑欧情绪的重要因素。何况在德国逐渐获得债务危机救助以及整合欧元区主导权的背后,还存在着英国面对欧陆强权崛起时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以及权力竞争的压力。因此在游说和谈判过程中,非欧元区国家将成为卡梅伦重点争取的对象,而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相信经济结构决定政治格局,那么打造一个某种程度上能够与欧元区分庭抗礼的非欧元区的权力中心,将经货联盟朝向经济-货币联盟的方向重新加以塑造,就并非不可想象之事,尽管这可能已经超出了一体化论者当初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