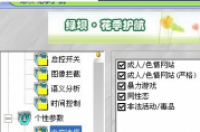2011年6月10日,这一天,对于《中国精神病收治的法律分析报告》撰写者、深圳衡平机构公益律师黄雪涛来讲是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她的当事人,曾轰动全国的从医院逃离后再次被抓回强制治疗的武汉炼铁厂职工徐武终于回家了。
湖北武钢炼铁厂职工徐武,因多年连续上访,被单位以“精神病”为由强制收治,四年后的2011年4月19日,徐武逃出医院,前往广州为自己“讨清白”,被诊断“自我评价稍低”、“抑郁情绪”,但未有其他更严重的精神病诊断。4月27日,徐武被从武汉前来的武钢保卫人员和武汉警察共七人从南方电视台大院强制带回收治。为了让徐武重获自由,黄雪涛多方奔走和呼吁。
徐武终于出院了,然而更令黄雪涛欣喜的是,2011年6月10日这一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我国首部《精神卫生法(草案)》,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近年来一直关注精神卫生立法的黄雪涛告诉记者,近年来时有所闻的“被精神病”事件暴露出一种制度漏洞,表现为精神病收治局面的混乱。甚至一些个案中,精神病人强行收治制度俨然已被某些基层管理部门视为一种另类管理手段,正是立法的缺失,使得权力的越界有恃无恐。
此次《精神卫生法(草案)》首先就是一部权利保障法,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得到医治的权利;其二,保障正常人不受精神障碍患者伤害与侵犯的权利;其三,保障正常人免于“被精神病”的权利。
黄雪涛介绍,《精神卫生法(草案)》明确规定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即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草案确认了精神病人拒绝住院的权利。同时,对违法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行为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周铭德,是上海市嘉定区居民,因母亲被误诊引发医疗纠纷,上访多年。2009年3月,周铭德在北京上访时,被截访者棍棒打昏、绳索捆绑后,送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当晚被注射镇定剂等多种药物,并一直被强制注射至出院。
两个月后,周铭德交纳4000多元“治疗”费用后,才以“外出治疗”名义获释。虽然他多番上诉索赔,但均被法院以“无法判断是否具备诉讼能力”为由驳回。
而近几年,各地的“周铭德”式的遭遇被接二连三地报道。
除了上访“被精神病”的外,还有因家庭纷争被自己的亲人送精神病院的。陈国明(化名),福建省邵武市人,2011年2月10日被妻子及妻子娘家人捆绑至南平市延平区精神病院。入院后陈国明与外界失去联系,姐姐费尽周折打听到其下落。在警方的介入下,陈国明住院56天后出院,但数百万元私人财产在住院期间被妻子转移一空,现妻子已提出离婚。
而与此相反的是,有许多真正的精神病人却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症精神病患者已超过1600万,大量的真正的精神病人被忽略,亟待救治。
2010年10月10日,两个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深圳衡平机构”发布了4万余字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
报告指出,一方面,许多应当被收治的患者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得不到治疗,或被家人长期禁锢,或流落街头,成为散落在社会中的“不定时炸弹”,威胁公共安全,同时这些患者本身的自由乃至生命安全也时常被侵害。另一方面,大量无病或无须强制收治的人,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承受丧失人身自由、被迫接受本不该接受的治疗带来的痛苦。
该报告还指出,我国精神病医学中存在诸多混乱现象,特别是精神卫生诊疗机构(也就是俗称的精神病院)正沦为报复和打压的工具。“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的情况导致了原本稀缺的医疗资源又浪费在了错误的人身上,而需要治疗的又得不到资源。公众不仅受到流浪精神病人的威胁,而且也受到被精神病院随时收治的威胁。
该报告执笔人之一、深圳衡平机构刘潇虎认为:“强制收治没有门槛、没有程序规范,个人无拒绝住院权利,‘谁送来谁接走’的出院规则,医院没有纠错机制等等乱象丛生。这不但为医生滥用权力提供条件,也为相关利益获得者提供了滋生公民‘被精神病’的温床。”
根据卫生部2007年的《精神卫生宣传教育核心信息和知识要点》,精神疾病有10大类、72小类,近400种,包括老年痴呆症、焦虑症、失眠症、人格障碍、智力低下等,这意味着这400多种精神疾病的患者都可以被强制收治。再加上“疑似精神疾病患者”,即未经诊断的人,其实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强制收治的对象。
由于卫生系统收治标准过低、范围过宽,在实践中,卫生机构的行业规则也没有对收治程序作出要求,医院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医院就可以把人强行收治起来。“这种收治方式与绑架无异。”报告执笔人黄雪涛说。
在黄雪涛代理的案件中,邹宜均是个十分特殊的例子。2006年10月26日到2007年1月26日,邹宜均在母亲的“陪同”下,在广东中山埠湖医院,以精神病人的身份,接受了整整三个月的治疗。
但被视为“精神病人”的邹宜均出院以后,却完全凭借记忆写下10万多字的《疯人院日记》,记述她被强制收治的整个过程,以及在精神病院的见闻。
出院后,邹宜均摆脱母亲贴身“监护”,离家出走,之后剃度出家。
2009年2月,邹宜均起诉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中山埠湖医院和她的家人,并聘请黄雪涛为其代理律师。然而令她们失望的是,该案在广州白云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官审查重点只在强制收治的动机和程序上,而不是关注当事人是否真的患病。
在黄雪涛眼中,邹宜均“有个性,有主见”,一直独立自主生活,与常人并无两样。其家人将她送进精神病院前,也未向法院提出申请。她认为,医院只能根据病人自愿原则进行收治。
几年来,黄雪涛收集了全国大量类似案例发现,由于我国《精神卫生法》至今未出台,中国精神病院收治病人毫无程序可言。有的先进行初诊,如果判断有精神病症状,就进行收治;有的不进行初诊,只要亲属委托医院收治,就被强制收治观察。
2005年12月20日深夜11点左右,在与妻子一番争吵之后,广州商人何锦荣没有经过医生诊断,就被妻子委托广州市脑科医院强制收治了。
那时,何锦荣有三家公司,还在广州的富人区二沙岛购有豪宅,身家上千万。
其入院记录显示,“2005年12月21日,据其妻子介绍病史,患者20余年前出现精神异常,表现为无故怀疑妻子有外遇,无故骂妻子,打妻子……”,“患者称可能有黑社会人员掌握其妻子把柄来整他,其妻子有外遇”。
根据何锦荣的说法,当晚,他坐在家中看报纸,妻子陈燕芳领着两个男人进来,他首先遭到一拳,接着被人勒住脖子,然后被铁链锁住。送进医院后,医生吴泽俊对绑在床上的何锦荣进行了对话初诊,并作了诊断记录。
但吴泽俊的初诊结论是,“未获感知觉障碍,接触合作,定向力好”,“思维清晰、连贯”,“意志行为无异常”,“未获情感方面障碍”等等。
2006年1月17日、18日,医院通知其妻陈燕芳来接人,但陈燕芳拒不接人,1月21日,医院同意何锦荣的母亲等家属来接,才办理了他的出院手续。
黄雪涛也曾经是何锦荣的代理律师。
她认为,何锦荣的遭遇,根源是医院缺乏自我纠错动力。如果医院发现收治的“病人”根本没病,或者不需要强制收治,而让“病人”出院的话,就要退还委托人预交的钱,这跟医院的营利目的是冲突的,因此,商业化运作的精神病院从利益上就欠缺自我纠错的内在动力。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精神病学被滥用,一些精神科医师也成了受害者。国内知名的精神病学专家、陕西省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纪术茂教授因为写信反映医院领导的问题,被自己所在医院诊断为精神病患者,这一诊断结果还写在了该院给上级部门的回复文件上。而诊断的依据,仅是医生的几句私下闲聊。
“如果精神病学滥用得不到有效抑制,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说,“我们呼吁填补中国精神科医师职业伦理空白,不仅是为了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也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权益。”
而黄雪涛告诉记者,其实精神病被强制治疗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法律规定明确,却没有被认真执行。
她说,民法通则规定,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若送精神病人强制治疗,需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宣告。而医学界普遍的观点是,精神病鉴定需要3到6个月,因此可能延误了精神病人的治疗时机。所以,现实情况是,大多数疑似精神病人被直接送治,几乎无程序可言。
2001年11月卫生部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对自己或周围构成危害者……应属紧急收治范围,并应给予特级护理。”
可以看到,民法通则的关于精神病人强制治疗需法院宣告的法律规定早已沦为一纸空文。
“被精神病”现象将得到最大程度的遏制
从1997年开始,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和张桂枝从当地乡镇政府逐级上访到北京。2003年10月,大刘乡政府几名工作人员从北京把徐林东接回漯河,并将他送进了驻马店市精神病院。他在驻马店市精神病院被强行捆绑48次,电击54次。驻马店市安康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2003年11月25日出具的一份鉴定书认为:徐林东属于偏执性精神障碍,建议住院治疗,加强监护。但是医院里很多医生都知道他没有精神病,还劝他不要去告状了,这样才能出院。
直到2007年7月,即徐林东被关进驻马店精神病院4年后,他的家属才通过其他村民知道他的下落,但却被告知无权接徐林东出院。徐林东住院期间,每月花费医疗费1000多元,六年半下来花费近10万元,这笔费用是大刘镇政府从民政救济款中拨付的。
2010年4月底,“徐林东事件”被曝光,伪造了徐林东入住精神病院所需有关证明的几位政府工作人员被免职。经过新任领导的同意,徐林东才得以走出他住了六年半的精神病院。
近年来“被精神病”之所以成为笼罩在公民权利上的一道阴影,就是由于随意化的诊治造成了公民权利的劫难。
此次《精神卫生法(草案)》首次明确了“不得强制进行精神病检查”的规定,对此黄雪涛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她说,这是一种根本性进步,其切实地赋予了精神病人“拒绝诊断”的权利。如果这个规定最终获得通过的话,将从立法上阻隔“被精神病”的发生。
记者从《精神卫生法(草案)》第六十四条中看到这样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对于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的,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离开医疗机构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评论员傅达林说,公民有“不被鉴定为精神病”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保障,不应当仅仅寄希望于医生的道德救赎。如果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如果医生可以对自己的诊断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很难确保医生不成为挫伤公民权利的工具。
《精神卫生法(草案)》通过立法的形式使精神健康的公民免于“恐惧”。
近年来,精神病患者被误收治的现象虽然仅是极少数,但将正常人误送、强送、误收、误治,而变成“精神病”竟如此轻而易举,已经引起立法部门的警觉。强治误治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此类违法行为影响恶劣,理当受到法律制裁。哪怕是监护人,若有意为之,就要定为诬陷罪、非法拘禁罪等。而今,在出台这部法律之后,还需尽快堵上精神病院收治的原有漏洞,并改善精神病患者的固有治疗方式,使其更加人性化、科学化、制度化。
但是要想杜绝“被精神病”屡发现象,还需要足够的配套措施来保护。
立法之后是不是“被精神病”的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黄雪涛对记者说,目前“被精神病”的当事人,救济渠道只有舆论救济,别无他法。但现在有了这个草案,至少看到了曙光。有了立法,就有了选择举证的机会。
但她同时强调,也不要幻想仅凭纸上的法案就能够一劳永逸。从纸面上的东西到实际操作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以平常心对待,不能太理想主义。精神病人的法律权利,从理念落实到立法,再从法律权利落实成为现实权利,需要一个过程。在其他精神卫生立法成熟的国家,也都经历了一个被滥用、立法、逐渐完善的过程。
“扰乱公共秩序”
作为非自愿住院标准引争议
2011年6月20日,中国精神卫生立法问题法律与伦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精神卫生医学领域、法律学者、社会公益组织和律师代表参加了讨论。
在专家看来,最新公布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非自愿住院的裁量权仍掌握在医学人士手上。
《精神卫生法(草案)》规定,患者对非自愿住院如有异议,可申请复诊、鉴定。
专家们一致对这条提出了异议,非自愿医疗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它直接限制人身自由,并迫使人接受医疗,长时间与世隔绝也使患者在心理上承受极大的社会压力。因此,判断是否有必要实施非自愿住院,同时涵盖了医学判断、伦理判断和法律判断。事实上,已经曝光的“被精神病”现象,几乎都有医生的有病诊断、鉴定人的有病鉴定作为依据,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非自愿住院仅仅以医学判断为准,没有考虑其中的伦理、法律因素,没有考虑人的社会属性(自由、尊严等)。必须将这种裁量权从医学人士手中移出,交给具有司法裁量权的主体,方能避免“被精神病”。
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教授认为,草案能否从根本上保护精神障碍者权利并杜绝收治过程中的权力滥用值得思考。精神障碍方面的医生只能提供专业的诊断和建议,至于说是不是应该被收治,以及如果当事人对住院治疗有异议都应该有相应法律进行程序上的规定。同时,法律应允许更多的民间组织参与到精神病患的救助中去。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认为,精神障碍的认定以及精神障碍者的强制住院或者非住院治疗在程序操作上都应当实行严格的司法化和去行政化,目前草案规定送治程序是行政化的思路,排除了司法的介入。
《精神卫生法(草案)》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非自愿住院的标准中包含了“扰乱公共秩序”,也就是说,“扰乱公共秩序”可以成为非自愿收治的理由。“公共秩序”含义可以极其宽泛,大到政治、经济、市场秩序,小到课堂、购票、交通秩序,以此为收治理由将对公民人身自由埋下深重隐患。
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方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精神卫生法(草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