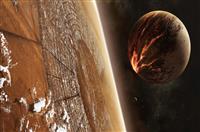1
“村长死了!”
我眯着眼睛,左手端着一杯水,右手中的牙刷有一下没一下地在牙床上敷衍着,我的邻居五哥撂下这个四个字儿,奔马一般从我家大门口一闪而过。我瞅着五哥的小身板儿一阵风似地在胡同尽头拐进了另一条胡同。
呵呵,我不厚道地笑了。村子里三千多口子人,每个人都盼着村长早点死,都盼了快二十年了,如今这个村梦都流行成了一句口头禅了,村长还不是照样张牙舞爪地活的好好的。我这刚起床,牙都还没刷完呢,五哥就开始发梦了。
“小个子被车撞死了!”
我正式睁开睡肿了的眼皮,这回是后街的二桥说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和我说,反正他也是说完就疾步往大街方向走过去了。
“小个子”是我们村长的“昵称”,一米六的小个头,实打实地装满了坏水,整完张家坑李家,在位十几年恶名昭著,村民没人喊过他的全名,背地里全都叫他“小个子”,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喊的却没几个人,二桥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因为二桥是直接的深受其害者,为了分地的事儿,村长仗势欺人,占了二桥家的地不说还带领着一窝儿堂兄堂弟狗腿子们把二桥家老老少少七口人打了个头破血流,全家在县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为这,二桥头上缠着白纱布去乡里县里告状跑了不知道多少趟,公道没讨下来半句,闭门羹吃了一锅又一锅。再小的地方也一样的官官相护,二桥不告了,回家用扫帚蘸了红土浆在自家过道的白石灰墙上写了大大的两个字:“报仇”。
我这才清醒了七八分,喝了一口水随意漱了漱嘴里的牙膏沫,顺手就把杯子剩的水泼在了门前的空地上。
“哎呀,泼的我这鞋面子上都是水。”凤英娘一贯的夸张语气大声说,“几点了小鱼,还刷牙呢,快去街上看看吧,村长让车撞死了!”
“你说真的呀?”我掩饰不住语气中的惊喜。
“可不真的咋地,死人都拉回来了,满街筒子都站满人了,快去看吧!”
我把牙膏杯子放在门墩上,撒丫子就往大街上跑了过去。凤英娘这回倒真是所言非虚,街上满满的都是人,人人都面带喜色地小声嘀嘀咕咕,比正月里的庙会还热闹呢。
“小鱼兄弟,啥时候回来的?”一个街坊大声向我打了个招呼,引得人群都向我这边齐刷刷瞅了过来。
“昨儿回来的,还不到24小时呢。”我应了一句,悄悄走到离我最近的一拨人里。
“真死啦?”我用城里带回来的八卦腔问,“咋死的?”
“酒驾!”聚丰压低了声音说,“昨晚上去乡里喝酒,开车回来和拉煤的大卡车撞上了。活该报应!一车上坐了四个人,其余三个都是头上擦破了点皮儿,就他死透了!老天睁眼了!”
聚丰的弟弟家和村长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得病死的早,扔下媳妇儿带着三个孩子,村长愣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地逼着寡妇改嫁,两个大的孩子不敢在家呆下去,去了南方打工,最小的闺女还不懂事就送人了。家破人亡呀!村长趁机把两家的墙推倒了,自家院子大了一倍。
“小鱼,你怎么这么会挑时候回来,正赶上看一场好戏!”二奎嘻嘻哈哈地打趣我,“还是咱小鱼威力大,三四年不回家,一回来就克死丫的!”
二奎的爹原本是村长的头号狗腿子,平时就好狗仗人势地欺负人,有一年春节在村长家吃席,本着自己人不外道地原则,顺走了不知谁送给村长的一条好烟。这下惹恼了狗主子,把酒醒了的二奎爹叫过来劈头盖脸地一通骂,连二奎那入土二十多年的爷爷奶奶都给捎上了。从此,二奎爹背叛了村长,还痛改前非地教育孩子们:狡兔死,走狗烹!
“喂喂喂,乱讲,我哪有那本事。”我罩着二奎屁股上踢了一脚,“要有,早克死这个败类了,还等到现在!”
“哈哈哈……”人群爆发一阵哄笑。
我的后脑勺一紧,头发不知被谁揪了一把,回头一看,我妈手里托了一块豆腐,一尊神像似的出现在了我身后。
“婶子,小鱼兄弟难得回来,就给吃豆腐呀?”开小卖部的冯林大声喊,“我家新进的肉,敬山的养猪场天不亮宰的生猪,来二斤?给小鱼兄弟八折!”
村长一家,上至老娘用的针线下至娃娃吃的棒棒糖都是从冯林的小卖部买的,冯林从来是帐都不带记的,因为村长家都来不给钱,记了也白记!敬山家的养猪场刚有起色那会儿,杀了一头猪,没给村长上贡,村长当时就黑着脸一句话没说。第二年,敬山的娘死了,老太太临死前交代拒绝火葬,敬山哥儿几个就偷偷把老太太埋到了祖坟里,坟头都没敢留,正赶上平坟扩耕,怕村长知道了罚款。不到一个月,村长还是知道了,浩浩荡荡带了乡里的人要把敬山的娘挖出来火葬。敬山的把柄落在了村长手里,乖乖交了五千块钱罚金不说,到底还是把坟挖开了。村长在乡干部面前现场充好人,说这么久了再弄出来火葬不太好,不如就在这样在棺材上泼了汽油,烧了再埋。
“冯木头,你个势利眼!”人群里有人喊了,“巴结小鱼兄弟是不?为啥不给我们八折?”
“街坊邻居们,一个村里住着,啥巴结不巴结的,我那里还有半扇子猪,谁要吃肉这就去我家,一律七折,仅此一天啊!”敬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嗷了一嗓子。
“好嘞!走着……中午包饺子吃喽!”立马就有人响应。
“有人出来了!有人出来了!”眼尖的章俊第一个瞅见村长家里走出了几个人,为首的是村长的好哥们,村里唯一的一家诊所的医生严发群,据说事发时和村长坐同一辆车上,命大,竟然逃过一劫。后面的几个都是村长的堂兄堂弟,按理说平日里好的恨不得穿一条裤子的兄弟,怎么个个脸上也不见伤心样儿。
“不偷着乐就不不错了!”人群里嘁嘁喳喳,“鞠清一八五的大个子,媳妇儿也比村长高出一脑袋,偏偏生出的孩子跟土行孙似的,瞎子也能看出来怎么回事!”
一八五的鞠清是“小个子”村长的堂弟,哥俩关系不错,村长媳妇和鞠清媳妇却是死敌,原因不明。
村长家里陆续有人进进出出,全是乡里和邻村有头有脸的人物,村民们向来嘴巴硬胆子小,见了衙门的人全都躲得远远的,有见识的人挨个向众人唱名,就是不见上去打招呼,大人物们也不抬眼皮瞅围观的人群。
我也是混在人群里的一员,从小在外面上学,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几年,见惯了人情冷暖,见多了拜高踩低,深谙什么叫惹不起躲得起,也知道敢怒不言的滋味。小又穷的村里死了头号人物,怎么说也算得上大事了,我有心把现场群众的言论视频发到网上的贴吧里,斟酌再三,没敢。我胆子小却鸡贼,不知道下一个接手村长大位的人是不是村长一族的人,他家上头有人,这都是极有可能的事儿。万一我把现场的众生相曝光了,惹恼了有权有势的人,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我走了容易,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呢,怕遭报复。我只敢混在人群里,人云亦云地跟风吐槽,适时地骂几句过过嘴瘾,我敢保证,当时我的嘴脸绝对是一脸的小市民德行,无耻之尤。
2
读大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姓苏的同学,南京人,爸爸在法院工作,那时候李刚他儿子还没有成为坑爹网红,苏同学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官二代,优越感十足,气焰嚣张胜过横行的大闸蟹。有一个姓曾的同学,父亲是当地的养鱼大王,曾同学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富二代,平时出手阔绰,从头到脚一身名牌可见其家资丰厚。平民出身的同学大多很会来事儿,砌词恭维者比比皆是,趋炎附势者也大有人在,一帮二十左右的小伙子们学着拉帮结派分成两组。我和班里的其余几个“丐帮弟子”被划分为第三世界。
一切似乎都无可厚非。费解的是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放任不管也就罢了,自己还主动向官二代和富二代各种示好。想想也是,市场经济了,老师也是人,情有可原。惨的是我们这几个第三世界的“丐帮弟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无主孤魂一样游走在两派之间,只有在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存在感才会分外的突出,那就是需要投票一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恰逢苏同学的生日,他的几个喽啰为表亲厚,大张旗鼓地给苏同学办生日趴,好事者纷纷共襄盛举,凑份子给苏同学买寿桃,哦不对,是生日蛋糕。一轮统计下来,苏同学一派全部出资出席,曾同学一派全部佯装不知,“丐帮弟子”除了躲没别的办法,没料到的是投资最多的竟然是刘老师。据说宴会盛况空前,结果人人大醉而归。苏同学回到宿舍以后,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一头倒在曾同学的床上大睡。曾同学回到宿舍以后试图摇醒苏同学,苏同学一抬头“哇”一声喷出了一大摊色臭味十足的七彩呕吐物,把曾同学香喷喷的床铺喷成了一个流动的垃圾桶。
曾同学当时就大发雷霆,无奈苏同学依然是一滩烂泥似的沉醉未醒。第二天,苏同学醒了时候,淡淡地对曾同学说了声:“sorry”,然后就没事儿人似的上课去了。我们几个“丐帮弟子”怕惹事上身,也前后脚去了教室。晚上10点左右,苏同学洗漱的时候突然破口大骂,言辞极其专业,无奈骂了半天也无人应战。第二天苏同学把这事告到了刘老师那里,刘老师亲自调查,我们几个“丐帮弟子”不可避免的成了被询问的目击证人。直到刘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完之后,我才得知骂架的起因:苏同学的牙刷上不知被哪个男同学涂上了男生自慰以后的分泌物。
这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奇事。讲真的,我听到之后曾经几度忍不住发自肺腑的大笑。后来我问其他几个“丐帮弟子”,他们一致表示,如果不是刘老师在现场,他们一定狂笑!实际情况是,我们忍笑的这个“丐帮弟子”证人,一律缄口:没见到任何人做这件事。刘老师试图将整件事小事化了,苏同学不同意,扬言要报警,还私下里把我们几个证人叫过去说如果帮着指证就请我们去海底捞搓一顿。我们这几个“丐帮弟子”为了果腹,强烈的动摇,想着要不要说出那天我们离开之后就剩了那谁还在宿舍,正在这个时候,曾同学偷偷塞给我们几个一张家乐福的购物卡,说是用不完,怕过期了。
“丐帮弟子”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会变成香饽饽。整个学期,我们就像拔河一样活在两派之间香艳丰盛的拉拢之中。无耻的我们个个成了煮熟的鸭子,各种嘴硬各种含糊其辞。唉,想想那待遇,我竟然至今也不脸红。
我是从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胆小怕事又厚颜无耻的呢?无从考究。只记得我上刚大学的时候还一个个性十足卓尔不群的人。自己这么评价自己还真不是完全地颠倒黑白,那时候的我真的是存了些许个棱角的。
我读的是一个文科院校,毕业生四年之后基本都是大大小小的公家人,素有第二衙门之称。学校里辩论风气盛行,我曾一路过关斩将从年级组战到全校组的辩论大赛上舌战群儒,我也曾在学生大会上响应老师的号召就热点问题侃侃而谈尽显书生意气,我还在学生自发的质疑教材费用活动中和学校领导们讲道理。就是从这件事开始,我突然转性了,对任何问题都视若无睹,对任何不平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直到近几年媒体大肆渲染“路上有老人跌倒竟然没人去扶,这社会真冷漠”的时候,我还跟帖说“你敢扶你去扶呀,反正我是不敢!”
3
读初二那年,班里有个叫傅增的男生,情窦早开型的,剃头挑子一头热式儿的暗恋着文娱委员小璐,小璐的眼神除了盯着黑板就是盯着我们班第一名文生,这是我这辈子见到的第一版活人三角恋。傅增有多喜欢小璐,小路就有多喜欢文生,这样的狗血剧情一点都没跳出当时火爆的琼瑶剧范畴,所以也就注定了傅增和小璐双双失恋。小璐是女生,失恋的情形极其典型,发呆,上课没精打采,成绩明显下滑。傅增的成绩本来就是前三名,倒数的,完全没什么可下滑的空间,他失恋的直接后果就是用自行车锁砸了文生的课桌。这一幕恰好被当天值日打扫卫生的我看到。
那天晚上八点半,晚自习结束后,一个被学校开除的初三生在学校门口拦住了我。
“你是关小鱼吗?”来人躲在学校大门的阴影里问。
我说:“是。”
“有人让我告诉你嘴巴严实点,别乱说话。”阴影里的人摞狠话。
我有点没反应过来,没吭声。
“不然你的课桌也保不住!”阴影里的人说完转身离去,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且看清了阴影里的那个人转身时的脸,就是那个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被校长点名开除的初三生。
从此我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安中,同时比我过的更为不安的是无辜加冤枉的文生同学,他是一个只会两眼盯在课本上的三好学生,被小璐莫名其妙的暗恋,以他的迟钝程度,全班恐怕他是最后一个知道这起桃花运的。至于他的课桌是如何被车锁砸的坑坑洼洼的,估计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更令他意料不到的是,这仅仅是他噩梦的开始。
那年冬天,文生穿了一件崭新的枣红色皮外套,无论是颜色还是材质,在当时都十分的扎眼,尤其扎了傅增的那双因嫉妒而终日红肿的眼睛。我熟知这件事的起因,很快就预料到了它的后果。
一次体育课上,体育老师临时有事让大家自由活动,多数同学选择了去操场放养自己,我嫌冷,没出教室。文生同学抱头扒在课桌上睡大觉。同时还有坐在最后一排的傅增,他的一双红眼思思盯着黑板上方的钟表上。我隐隐觉得不妙,正想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就在那时,傅增从自己的位子上起身,快步走到文生的座位后面,右手的铅笔刀飞快地在文生的后背上比划了一下,旋即走向教室门,离开。整个过程不到半分钟,文生的枣红色皮衣上多了一道刺眼的划痕,和皮衣的亮闪度一样吸睛。回到教室的同学们都看到了文生后背上的那道裂痕,只有文生恍若不觉,放学以后照常回家。下午再来的时候,文生的上衣换成了一件普通的棉布料子。文生的妈妈和他一起来到学校,直接去了班主任的办公室。那天放学,班主任把全班学生留在教室,一个挨一个地询问体育课时都去了哪里。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拉肚子去蹲厕所了。后来,傅增在我的课桌里放了一张纸条,我没打开,直接撕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讨厌自己,第一次鄙视自己的内心,第一次感觉自己和傅增那类人一样可恶,连带着,我也恨屋及乌地捎带上了小璐。初中毕业时,大家相互在笔记本上写留言。小璐的笔记本传到我手里时,我写了这样一句:“我讨厌你,是你让我开始讨厌自己。”
后记
村长死那天,整个村子里就像过年似的那么热闹,敬山家的猪肉不到晌午就卖光了,冯林小卖铺的鞭炮也跟着脱销。人人唱和谐的今天,基层老百姓却民怨冲天。我离开村子后,听说村长家的儿子成了孤家寡人,同龄的孩子自发疏远他们,上一代不积德,下一代遭殃。我努了一把劲,去百度上我们村在外务工人员建的贴吧上去PO那天现场老百姓的畅所欲言,迟了,有人抢先贴了上去,有图有真相,详尽至极。我很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