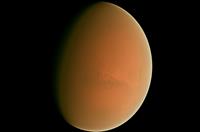左起:陶铸、陶斯亮、曾志
父亲离开我快四十年了,就连我去合肥接父亲的骨灰回京也三十多年了,但无论时间怎样飞快地过去,在我的耳边时常响起父亲在弥留之际对我的呼唤。在合肥的一所部队医院里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度过了他四十三年革命生涯的最后四十三天。每每想起这些,我不由得百感交集,万箭穿心,泪如雨下……
第一次见到父亲,我吓得大哭
父亲和母亲是在白色恐怖中相识的,由于革命的需要他们组成假夫妻,建立了“家庭”。渐渐地两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假夫妻假戏真做,最终终成眷属。再后来就有了我,父亲给我取名叫斯亮,意思是“这儿,最光明”。
我出生在延安,是苏联妇科医生安诺夫给我接生的,有好多在延安的小孩儿都是他接生的。生我时母亲子宫大出血,差点儿死掉。生下我不久,母亲又因为整风运动被隔离了,不许回家。所以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承担起了对我的抚育。
在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派往东北,他们当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父亲把年幼的我留在延安保育院,托付给一位曾给朱德当过马夫的杨叔叔。记得父亲对杨叔叔说:“我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你把她带大。”出发那天,在延河边上有许多人给我父母送行,母亲是一步一回头,留着眼泪和我告别的,而父亲就是抱着我亲了一亲,转身就走了。
这一年的8月,日本宣布投降。父母亲迫切想见到我,就给延安发去电报,希望杨叔叔能把我送到东北。但延安和东北相去万里之遥,之间虽有安全的解放区,但并不安全的国民党统治区更多。为绕开危险的国统区,杨叔叔带着我先绕道至晋察冀解放区,继而南下邯郸,再东行烟台,然后渡海至大连,最后改乘海轮取道平壤,再转回安东,最终到达辽吉省委的所在地白城子。这一路,我几次病重难治,几次险些走失,又几次险象环生。一个40多岁的残疾军人和一个5岁的小女孩,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硬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成了一段传奇之旅。那时候没有“钱”的概念,杨叔叔就拿着介绍信,指着我说这是陶铸同志的女儿,要去东北找父母,请你们一路上照顾。一封介绍信,就这么一路走天下。走到张家口,胡耀邦在那儿,给了我们一些盘缠,但主要还是拿着介绍信办事,好像运包裹一样,一站一站运过去。
走了一年,我们到了东北。那时父亲在辽宁当省委书记,他原来以为我死路上了,已经把我的相片挂出来当遗像了。我们去找父亲的时候,他正在开会,一听到门卫报告,他高兴坏了,一下冲出来,一屋子开会的人都跟他冲出来。我被那阵势吓傻了。父亲一把将我抱住,我害怕得直哭。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杨叔叔,第一次见到父亲,我却一点不留情面,以号啕大哭来对待他。
在家里,我和父亲是“两口子”
父亲是一个坚强而豪爽的人,然而在对待自己的独生女儿时,七尺男儿却换上了一副慈母心肠。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忙忙碌碌的,但只要一有时间和精力,他就会把关爱放在我的身上。
我的学生时代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甚至小学六年级时还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天天要等到他回来才肯睡觉。我们在东北的时候,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每天晚上父亲都会为我烧好一盆洗澡水,等我洗好了,他再用剩水接着洗,在父亲看来,女孩子就应该用干净的水洗澡。后来父亲调到广东工作,那里天气又太热,我晚上睡觉总不爱穿睡衣,父亲每天不管多晚回家都要来查我的房,叮嘱我把睡衣穿上,把蚊帐放好。父亲希望我打扮得漂亮一点儿,平时我要是梳头梳得太板正,他还会给我弄乱一点儿,然后看着我说:“这样才漂亮嘛。”父亲甚至不允许我光着脚走路,担心脚趾头长开了不好看。当时年纪尚小的我搞不清楚“两口子”是什么意思,有人问我家里几口人,我就说:“就我和我爸我们两口子。”
除了生活上的关心,父亲还定期给我总结优缺点,让我坚持写日记,并亲自给我改日记,有时自己改不过来就让秘书帮着改。有一次,我们全家从越南回来,父亲对我说:“你给胡志明伯伯写封信,感谢他热情的接待。”我写的时候,抓耳挠腮地想不出什么好词来,忽然抬头看到卧室里有一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招贴画,就把这句话用上去了,然后拿给父亲看,他看到这一句,马上批评我说:“这句话怎么能用在这儿呢,不对不对,你一个小孩子家,怎么能跟革命领袖称知己呢?”我不服气,说“怎么就不能称知己呢?”父亲坚决地说:“肯定不对,一定不能这么用,赶快删掉。”
我也许是受了有诗人气质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文学。上中学的时候,就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或者历史系。但是这种天真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是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他深知在那个年代学习文科很容易犯错误,政治风险大。于是坚持要我在选择专业上务实一点,争取有一技之长,并强烈建议我学医。当时的我并不明白父亲这样的苦心,但是拗不过他。1962年我从广州执信中学毕业后,考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去学校报到的前夕,父亲对我说:“亮亮,你知道‘相依’这个典故的来源吗?”于是,他就给我讲了李密《陈情表》的故事,然后充满深情地说:“亮亮,我们也是相依为命的父女,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爱你,但是爸爸对你没有任何个人要求,只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相信你不会辜负爸爸对你的期望。”
父亲对我的爱是不加修饰的,他的牵挂,他的担心,他的温柔都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而我母亲总是一本正经的,每当父亲给我讲故事,跟我聊天,或是有时抱抱我亲亲我,她总是在一旁静静看着我们,很少插话。所以在家里,我是永远的“爸爸派”。
唯一的一次,我和父亲是胜利者
我父亲是1967年1月4日被揪出来,那时我还在上海,当天晚上两三点钟,同学把我叫起来,给我一张油印传单,上面写着“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我一看,知道完了,父亲出事了。这一切变化太快,我心理上完全调整不过来,忽然就体验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有一次在中南海同时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我父亲三人,一大群人突然冲进屋子,把我父母带走了。我坐立不安。有个警卫说,你跟在后面悄悄看,没事的。我就去了,看到那群人这个按一下父亲的头,那个按一下父亲的头,他还老是很倔强地挺起头来。他们声色俱厉地喊口号,批斗他。父亲回来后,我端了盆洗脚水,想给父亲泡泡脚。结果看见他头上有一个大包,是刚才批斗时打出来的。我扑上去说:“爸爸,我给你揉一揉。”他一下把我甩开,愤怒地叫道:“如果我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就跟他们拼了。”又叫道:“要批斗就批斗我,为什么把曾志拉去,她是个病人。”说到这儿,父亲流泪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他是心疼我母亲,我母亲那时候患有甲亢。
后来他们不提“保皇派”的问题了,直接说父亲是叛徒,给蒋介石写过信,出卖过同志,又在南京监狱写过悔过书。这些都是我伯伯揭发的,看着满大街的大字报,把我也弄糊涂了。我那时候挺革命的,就去问父亲,希望他给我一个斩钉截铁的答复,我一脸严肃地问父亲:“你有没有出卖过同志?”父亲当时特别伤心,看着我说:“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了吗?我愿意把自己的血洒在地上,来证明我没有出卖过同志!”我到现在都记得父亲当时看我的眼神,我觉得他特别屈辱,因为只有受到最大委屈的人才会有那种眼神。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遭到那样的对待,实在太让人心酸。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怀疑过父亲。
有一天,一个警卫破门而入,勒令父亲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父亲可能背错了,警卫就把他臭骂一顿,立即上纲上线,呵斥他说:“你对毛主席如此不恭,连语录都背不出,你是怎么对待毛主席的。”把父亲批得一塌糊涂。然后那人自己又念了一段语录。我天天在学校念毛主席语录,记得特别熟,当时我在房间里一听那人也念错了,赶紧找出语录本,翻到那一页,拿着语录就冲出去,朝那人说:“你也念错了,你是怎么对待毛主席的,你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那人顿觉尴尬,灰溜溜地走了。那人一出门,我和父亲就哈哈大笑,父亲还夸我:“小亮亮,你还真行,看来以后你能当我的秘书。”那几乎是父亲受迫害后唯一的一次放声大笑,我从没见他那么开心。印象中只有那么一次,我们觉得我们是胜利者,大多数时候我们总是被整得很惨。
我与父亲的生离死别
在和父母亲短短一个月的相聚之后,我接到工作分配通知,只身前往东北一所军队医院任职。离家那天,我没有跟父亲告别,我怕见他,我知道自己肯定会哭。没想到,这会成为我永生的遗憾,因为这一别竟然是和父亲的永别。父亲去世以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上密密麻麻批了很多字,最后一句是:“9月13日,女儿离家之日。”说明他已经知道我要走了,那一晚上通宵没有睡。
父亲明知患了不治之症,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对母亲说:“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但是这个时候,中央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把当时许多被打倒和半打倒的老帅送到外地。父亲被疏散到合肥之前,母亲接到指示,让她或者随父亲一起南下,但从此不得与我有任何联系;或者选择永远地离开父亲,还能和我保持联络。
母亲跟父亲商量,父亲说:“你还是跟亮亮去吧,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跟着我也帮不了什么忙。”就这样,他们决定让父亲一个人去合肥。当时他们都知道这是生离死别,是最后一面。
从接到通知到离开只有三天时间,这三天他俩表现得非常理性、克制。父亲以为他们会让他去农场住,就让母亲给他准备雨鞋、雨伞、被套。临走那天,母亲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父亲已经肠梗阻了,根本不能吃东西,但是为了感谢母亲这份情谊,他硬是吃下去了,每吃一口,就流一头的汗,吃这顿饭花了一个钟头。
父亲跟母亲说:“你告诉亮亮,我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她要知道,爸爸在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他要了我妈的相片、我的相片、我儿子的相片,拿纸包起来,揣在贴身的内衣口袋。父亲说:“我带上相片,就能感觉到跟你们在一起了。”打了一支杜冷丁,他就上路了。
我们住在招待所,广州军区的人奉命通知我们,说陶铸死了。母亲当时很镇定,没有流露一点痛苦的表情,只问:“那我们能去看看吗?”他们说:“不行。”我忍不住了,冲到厕所里哭,待在厕所里不敢出来,因为不敢当他们的面哭,否则又会被说跟陶铸划不清界线。后来听105医院的医生说,父亲去世前直喊我的名字,说:“让我女儿来”。
我做梦老梦见父亲,可是很奇怪,在梦里俩人总是碰不到一起。我很想告诉父亲,他的冤案已经得到平反昭雪,他当年许许多多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今天都实现了,他当年所有困扰的问题现在都解决了。农民生活不好,吃不饱饭;生产力上不去,没钱修路、修桥……曾经让他操心、让他痛苦的所有一切现在都不存在了。我还要告诉父亲,虽然他已经走了四十年,但家乡的人民没有忘记他,他们把对父亲的爱都放在我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