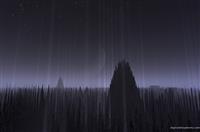高举蹬着自行车,漫不经心地。田间的小路凹凸不平,好像有意为难他似的,搅得车轮咯咯噔噔。他在车座上一会儿弹起,一会儿落下,一会儿又弹起,一会儿又落下。两旁的麦浪晃荡着他的眼。陈组长的脸倏悠伸出来,倏悠又缩了回去。高举感到好烦心,总觉的它里面有某种目的,或阴谋,间或还有点调侃,有点轻蔑。这些感觉在高举的脑海里,在高举的心里,乱腾腾,变幻莫测。他使劲摇了摇车把,唉,也许她是好心的吧,高举却这样安慰自己。
陈组长是学校语文教研组的组长,近五十,很富态的女人,整个教研组里数她年龄最长,资格最老。高举第一天去学校报道,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她。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高举,笑道:呀呀,这身学生皮该脱下来啦,一个在本本的本科生,怎么能穿得这样拖拖拉拉的。高举不好意思地扯了扯衣角,犯错的学生似的晒在了太阳下。第二天,还没进办公室,高举就被陈组长夸张的言行堵在了门外。她拿着一套全新的“耐克”,蓝底白杠,硬扯着他换上,毫无商量地拉着他去了校长家。
“校长的女儿”,这个羞辱的字眼击打着他的自尊,一股莫名的悲哀漫过心头,他猛一用力,车链脱了槽,卡住了,车子翻到在地,他也顺势跌倒在麦地里,麦苗扑啦啦卧倒一大片,陈组长的脸也跟随着倒下来,缠绕着他,他烦心地吐了一口,撑着手想站起来,一只飞虫撞在眼球上,他双手捂住眼,匍匐在地,任由泪涌。校长的女儿,那个跛足的女孩对他是个侮辱,这份侮辱一点一点从他的心底升腾,击打得他脑浆开花。我高举再穷,我毕竟是堂堂的大学本科生,也不至于连个健全的媳妇都讨不上吧?你陈组长也太瞧不起人啦!他心里恨恨地。陈组长的弥勒脸变换着表情,大学生有啥了不起,北大生还卖猪肉呢。别把自己看得多粗多长,校长是啥份量?高举心里恨恨的,面子上还笑着,我也没把自己看高,但也不至于找个跛足的老婆吧?
高举的爹死得早,在他已没什么记忆。只有母亲,他生命里只有母亲。寡妇熬儿,日子的苦头他是深味着的。别的孩子玩,别的孩子追女孩,他不敢,没有父亲的自鄙,使他不自觉地低眉顺眼。但这份苦又莫名地折磨着他幼小的心灵,他渴望挣脱,渴望改变,他想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只能挑灯苦读。孩子们欺负他,嘲笑他,他默默地承受,躲避。只有小梅常常挎着书包到他家来,和他趴在案板上写作业。有时小梅把热乎乎的鸡蛋塞进他手里,他都不敢正眼去看她,他害怕自己分心,努力地克制自己,钻进题海里,写啊,算啊,天昏地暗。这一切恍惚还在。
夕阳挪了挪方向,正好照在他伸出的手指上。那只飞虫湿漉漉地粘在手指肚上。他厌恶地弹下拇指,飞虫死踏踏地落进麦浪里,他心里有点得意,拍打拍打身上的泥土,推起车子回家去。
母亲正侍弄着锅灶,热气腾腾的。小梅扯着孩子在和母亲说话。他上大学了。小梅初中没读完就下地干活了,很快嫁到西村,孩子都四岁多了。小梅还像以前一样,常常到他家来,多是和母亲唠嗑,东家西家的日子,偶尔也有高举,关心着他的婚事。“蛋蛋,快看舅舅放学啦!”看到进院门的高举小梅高兴地指给孩子。高举放倒自行车,拍拍手,“蛋蛋来啦,蛋蛋又长高了。”他想去抱下蛋蛋,眼光却瞟住梧桐花影下的小梅,花影绰绰,燎的他心旌摇曳。他赶紧收回眼神,进屋拿出工具,上他的车链子。有风吹来,一朵梧桐花展了展腰肢,浮在他的头发上,蛋蛋欢呼着攀住他的脖子,翘脚去够。蛋蛋肉嘟嘟的胳膊摩擦着他的脖颈,痒痒的,漫溢出一股暖流,那是一份父性的本能温暖,他吻住蛋蛋的小手吹出气泡,嘙嘙地响。蛋蛋乐得翻倒进他的怀里,母亲看着他俩,叹了口气喊吃饭。
他头也不抬地扒拉着饭,陈组长的脸荡过来,荡过去,他努力地把脸压低些,囫囵吞枣地发着响声。母亲坐在一旁,没动筷子。她唠叨着闷在心里的话。小梅才比你大一个月,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啦,你连个媳妇影儿还没有呢,我这熬到啥时候有个头呢?在母亲面前,他是自由的,松弛的,他放下筷子,给母亲挤了挤眼,老娘你放心吧,儿子会把媳妇给你娶回来的,你安心等着抱孙子吧。母亲伸手想拧他的耳朵,没够着。
母亲拉巴他成人不容易,他是深味着的。他考上大学,五里八庄是响当当的。人们赞呢,这老高家的,寡妇熬儿,可熬值了。母亲脸上,心里乐开了花。母亲越来越老了,一辈子没过过好日子,他不能再让她操心了。
月亮游移在花叶间,影影绰绰。高举拉了拉窗帘,坐在桌前想备会课,陈组长的脸倏地伸了出来。昨天给你说的事考虑得怎样啦?时间总在不觉间,与陈组长在一个办公室已近大半个学期。自从有了“校长女儿”那样的不愉快,高举心里有堵墙似的,时刻堤防着这个老妇人。他心底深处对她还一份轻蔑,不单对她人品浅薄的轻蔑,更多是对她知识水准匮乏的轻蔑。他曾愤世嫉俗地想,国家真是瞎了眼,每月浪费那么多纳税人的血汗钱,养这么样的教师,误人子弟。这样的情绪漫溢在他心里,翻滚着嘲笑的浪花。但面子上他还是笑着,谢谢您老的关心。
陈组长的丈夫在政府部门,具体哪个部门高举不太清楚。他还处在幼稚的学生时代,世事的节节梢梢他还没有涉猎。尽管学生时代对美好前程的无限畅想常被现实里的工作生活乏味着,但他还是持有幻想,知识改变命运,黄金屋在书里,颜如玉也在书里。他在这所中学的教师队伍里学历最高,知识水准最深,语文课讲得一片叫好,他心里得意,只是陈组长时不时地敲打他:别太书呆子气啦,你再有才,领导不用,也是一把烧锅的料。开始,陈组长说这话,他心里鄙夷,现实的工作生活渐渐地渗透给他一些可意味不可言表的情愫,这些情愫缭绕着他,撩的他的自尊心隐隐作痛。校长把最差的班交给他,在大会上提名批评他;老师排挤他,对他的优秀不是赞扬,而是调笑。这些不可言表的伤害一点一点地浸润着他美好的灵魂,他心里暗暗觉着陈组长是好心的,也许她是好心的吧!昨天陈组长一天几次地伸着脖子,我家那口子反复强调了,这次你一定要抓住良机,这可是我们县纪检委书记的女儿,这事要成了,你前途无量啊,小高同志,一定要三思啊!
高举盯着窗外,月儿斑斑驳驳地散着,满院的梧桐花在绽放,他好像觉着它们在颤抖,在哭泣,他好想问问花儿,你的绽放很疼痛吗?花儿无语。他心疼地闭上眼睛,拉灭灯,展开双臂想好好睡一觉。陈组长的话语似乎又亲切起来,你在大学都读些啥书,没听过先人还是什么大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吗,什么什么来着,既然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何必要拔地而起呢?这是多么精明的人呐。学而不用则罔啊。陈组长说这话时,他正在吸墨水,手一紧,大滴的墨水从笔尖吐出,落在他的备课本的封皮上,骨碌碌滚了滚,停在梦幻娃娃微眯着的眼里。他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着陈组长,这张弥勒脸第一次让他觉着敬重,是啊,这话太深刻了。读大学时,他喜欢过一个女孩,是大市的,官二代。从小没有父亲,过着贫穷日子的他,自卑,迫着他,不敢表白。那时的他曾在日记本的首页写着:既然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何必要拔地而起呢?!每天默念几遍,他似乎想从中领落点人生的奥妙,想让它给他点勇气去表白。但在女孩面前,他感到了它的肮脏。最终这份爱夭折在他纯洁的灵魂里。现在这句话从陈组长嘹亮的喉咙里响起来,他感到好亲切 ,又有一股力量漫过他的身体,他用枕头压住脸,嘿嘿地笑了,坏坏的。 他比公鸡起得还早。洗脸,刮胡。拿出新买的一套行头:银灰色的西装,粉红色衬衣,海蓝蓝的领带,棕色皮鞋。人是衣马是鞍,真理!潇洒倜傥,还有更好的词吗?高举对着镜中的自己打了个响指,自信地走出去。他没有骑自行车,也没去学校。他乘上大巴,去了陈组长家。
陈组长的家在政府机关的家属院,上下两层小楼,带个小院子。看到高举,陈组长的眼眯成一条缝,肥硕的臀夸张地扭动着,语音高昂:呀!呀!呀!帅呆啦。这大学生就是不一样,腹有诗书气乱爬啊!她对着楼上喊:我说那口子快下来,我们学校的大才子大帅哥来啦!
陈组长的那口子精瘦,矮小。与陈组长形成两个极端。用余秋雨的话说,就是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他透过眼镜片上上下下打量着高举,不错,张书记会喜欢的。高举挺了挺胸笑笑。他这次稳住了自己的性情,不像见“校长女儿”那样轻率。他的耳际始终有一个嘹亮的号角:既然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何必要拔地而起呢?!陈组长的那口子不是好榜样吗,不也是攀了陈组长爹的肩膀吗?有名有利,人活着还想啥?半年多来的现实生活,高举的激情澎湃被阻隔,思想里流进些渣汁。爱情,曾经给他多少向往而美好的爱情啊,怎么到了现实的物质里死踏踏没了感觉了呢?他正了正自己的领带跟着陈组长的那口子上了楼。 沙发里坐着一个女孩子,学生头,忽闪着大眼睛,粉色的连衣裙外搭白色的坎肩,看上去文文静静有点稚气的女孩。陈组长乐呵呵地端着果盘招呼着,高举啊,你要珍惜,这可是我们书记的宝贵女儿呢。她拍拍高举的肩膀找个借口下楼去。女孩直挺挺地坐着,高举问她话,她伸伸舌头笑笑。高举给她递个苹果,她吓的缩着身子,不不,妈妈说的不能乱吃别人的东西。高举感到好笑。他的眼前交替出小梅和大学女孩的脸庞,那是能让他激情,渴望触摸,渴望亲吻的脸庞。可眼前这张脸,就像行走在大街上的人,陌生的和他毫无关系。他使劲掐了掐脑门上的皮肉稳住自己,任思绪飞旋。
清晨的阳光从窗子里直洒进来,高举坐在办公桌前,盯着备课本上的梦幻娃娃的眼睛,墨水已干在她的眼脸上,模模糊糊。陈组长的脸伸了过来,小高同志,女孩漂亮吧,这可是政府大院有名气的漂亮。再说,人家的家庭多硬,那可是纪检委书记,一手遮天的。我那口子说了,现在政府办公室正缺一位县长秘书,你正合适,中文系本科生。这事成了,做秘书没问题。好好想想吧,小高同志,前途无量呢。陈组长嘹亮的声音夸张着,喧腾着,诱惑着,缭绕着高举的脑际,直到月亮挂上枝头,他斜靠着床头,头好痛,他用双手捂住脸使劲地揉搓。
生活就是这样的现实,人在与它的磨合中,总是人妥协。面对着这个有点脑残的女孩,他不再有“校长女儿”给他的屈辱,他只是觉着可笑。他眯起眼,甩甩头,耳边奏起一曲嘹亮的号角:既然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何必要拔地而起呢?是的,何必呢?她虽然因脑炎留下点后遗症,虽然中学的学业都没完成,但她有大学的文凭,有个政府档案局的美差,有个可靠的肩膀,一个好爸爸。不然,你高举能摸得着这漂亮的姑娘,自己穷家破院的,有什么好挑剔的。爱情,笑话,见他妈的鬼去吧。高举思想里活跃着。这次陈组长的脸伸出来时他挤着眼向她点了头。陈组长的弥勒脸荣光焕发,哎呀呀,小高同志,这才是精明人呢。 落进现实里,高举感到了陈组长的亲切。她的“一手遮天”的言论不再夸张。不费吹灰之力,他坐上了县长秘书的宝座。他的夜晚,不再是昏暗的灯光,简陋的硬板床。他住进了全欧化的豪华建筑里,水晶流雨似的灯饰,璀璨迷离;梦娜丝的柔软使他的心旌摇曳。他嗅了嗅身边的肉体,饿狼般地扑上去,雄性大展,肉体惊骇地嘶叫,他不管不顾任自己疯狂。他尽情享受着物质和肉体带给他的幸福和快乐。他从小忍辱受屈,受苦受累所渴盼的不就是这样的幸福和快乐吗?
他开着小轿车行使在田间的小路上,五里八庄又一次沸腾了,人家寡妇熬儿真是熬出太阳来啦!高举坐在小轿车里得意地笑。他嗅了嗅麦苗的清香,泥土的气息依旧。他看到一群放学回家的孩子,飞快地蹬着自行车,他看着他们从车边飞过,曾经的屈辱涌向心头,他猛加油门,飞驰而去,飞向他人生的竞技场。
政府办公室宽敞明亮,茶雾缭绕。高举坐在临窗的办公桌前,拿张报纸半遮着脸,静静地暗察着这儿的人与人,体味着人与人间微妙的言行。他感到了一张张可爱的脸。那些在书本里曾经憎恶,嘲笑,呕吐过的脸,在现实里都可爱起来。变色龙,势利眼,哈趴狗都可爱起来;甚至奴颜媚骨这样的贬义词在这儿也褒义起来。陈组长说过,在政府机关里混,奴颜媚骨是必须的,这年头,谁不奴颜,谁不媚骨呢?是的,知识浅薄的陈组长毕竟在政府大院里长大。他开始嘲笑自己,什么廉洁奉公,高风亮节,忠厚实干,幼稚吧,你高举不是幼稚,简直是白痴。一段时间的秘书工作,高举的思想不断的倾斜,他努力把自己向现实靠拢。他毕竟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中国的文学博大精深,最有实用价值的就是用到歌功颂德上。他大笔飞舞,一路高歌。领导高兴了,他的岳父大人更是喜上眉梢,他大权一扬,给他一只跳板,派往乡镇任职书记。环境造就人,不到两年,他在各种场合已是游刃有余,高举有时都惊诧自己的适应能力,他感到得意,十年寒窗什么也没学到,还是社会这所大学给人的东西真实,名利双收。看到他的优秀表现,岳父喜在心里,在自己退二线时烧了最后一把火,利用自己的关系把这个得意的女婿提到了城建局局长的宝椅上。 城建局局长,在城市开发的浪潮中举足轻重。高举坐在办公桌前,旋动着皮座椅,享受着权力给他的荣耀。他在这儿可以号令三军。他看到一张张羡慕,讨好的面孔,他心里得意。从小在人前的低眉顺眼都得到了报复。中国男人的皇帝情结在他身上实现,整个的白天都属于他,他高高在上,心花怒放。但在月亮爬上树梢的时候,人间慢慢安静下来的时候,他的心却是空洞洞的,繁华过后的寂寞。这份寂寞莫名地噬咬着他的心,特别在家里,面对那堆空乏的肉体,这份寂寞更强烈,强烈地噬咬着他的精神世界,那个曾被文学修养着的高雅的精神世界。噬咬地他难耐,他要崩裂,他咆哮着扑向那堆肉体,肆虐她,恨不得撕裂她。看着那堆颤栗着的肉体他哈哈大笑,但心底更寂寞。
看到周倩的第一眼,他寂寞的心海一点一点地泛起浪花,慢慢地喧腾起来。他痴痴地看着她,痴痴地。他努力按住宝椅扶手克制住自己:坐,坐吧,你就是来实习的大学生吧!周倩大方地回答:是,我叫周倩。高举笑了:是,周倩。你不说我还觉从外面飞来一只小蝴蝶呢。周倩闪动着一身的粉红坐了下来。好漂亮的小姑娘,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你是林心如吧!高举故意低垂着眼脸不看周倩,手里翻动着桌上的简历:是,周倩,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呵,说起来咱俩还是校友呢。周倩看着眼前这个高大俊朗的局长,心里也在闹腾,原来“风流倜傥”这个词就是为这个男人造的吧。她斜弋了高举一下,站起来敬了个军礼:请高局长下指示吧!高举压制着内心的荡漾,欢快地回到:好啊,从今天起小周同学担任我的奴仆,为我倒茶续水,扫地,擦桌子。周倩咯咯地笑。
夜色里的高举,寂寞的心快乐起来,他不想去看那堆肉体。权力,地位给他的快乐是白天的。黑夜来了,他渴盼爱情,周倩,这个小妖女给他带来了,他渴盼已久的爱情,如山洪爆发,他无法抗拒。 天还没亮,他就去了办公室,一个人趴在办公桌上。周倩满脸阳光地踏进办公室,看到趴在桌上的高举,心里顿了一下:咦,高局长昨晚没回家?
高举抬了抬迷离的眼睛:你个小妖精搅得我睡不着,你看我的眼睛都红肿啦。周倩凑近想看一下他的眼睛,一只手被抓住,她想挣脱,但却没动。高举顺势欠起身,把她扯进怀里,痴痴地盯着她美丽的脸庞。他的心好快乐,好幸福,生平第一次感到了爱情给他的美好,他轻轻地添着她的唇,她乖乖地俘虏着。他笑她,你真像个妓女。她咯咯地回,杜拉斯说女人不做作家,就做妓女,我甘愿做你的妓女。爱情就是这样没有理由,两个人很快泥成一团。也许是文学的共同打造吧,两颗心相溶着。他们谈古典文学的美,论当今文学的沦落。他们谈李煜,李清照,还有杜拉斯。提起张爱玲,她扭着他的鼻子,你怎么越看越是胡兰成?高举诡秘地笑,我是胡兰成,你要号召日本再次侵略中国。周倩,陷进了爱河里,她看着眼前的男人,仿佛是在梦里寻了很久的灵魂。她娇柔地搂住他的脖子。
高举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周倩,这个美丽的女孩,她是有肩膀的。她的叔叔是省长,她来这里实习只是一个跳板。高举深明这一点,他再一次为自己吹响了号角:既然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何必要拔地而起呢! 与周倩结婚后,高举做了市长。人生得意。月亮悠闲地游荡在星空,万物宁静,他酥在娇妻的肉体上,眯着眼乐。那支号角优雅地奏响,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从身下白晰的肌肤上跃起,体纵横交错地闪烁着,醒目,亲切,很曼妙。陈组长的弥勒脸也越发地可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