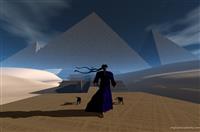
大约一个月前,有两个年轻人来我这儿,要我的小册子。他们一个头戴鸭舌帽,脚穿树皮做的鞋,另一个戴着制作精良的黑礼帽,但有点旧,穿的皮靴有点破。他们告诉我,他们来自莫斯科,是工人,因为参加武装起义而被迫离开那里,说话中流露出十分自豪的样子。一路上来到这里,被雇佣在这个村的果园里当守卫,干了还不到一个月。昨天园主把他俩辞退了,原因是他们鼓动当地农民捣毁果园。他们带着微笑否定了园主的说法,说他俩只是晚上到村里转转,跟当地农民聊聊天,并没有鼓动谁干什么。
他俩,特别是那个显得更活泼一些的,笑的时候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露出一口白牙,都读过不少革命书籍,因此在谈话时满口专有名词:演讲家、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剥削什么的,不管使用是否得当。我问他们读过一些什么,那个皮肤稍黑的笑着回答:读过各种小册子。我问是什么样的小册子。回答是:“什么样的都有,例如《土地与自由》。”我问他们读后的感想。皮肤稍黑的回答:“里面写的都很对。”我问:“对在什么地方?”回答是:“说明生活已经无法忍受了。”我继续问:“为什么无法忍受?”他们回答:“这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土地,又没有工作,老百姓不为什么就受到政府的残酷压迫。”
接下来他俩互相打断对方的话,抢着说哥萨克是怎样用鞭子抽打老百姓,警察是怎样胡乱抓人,甚至把那些无辜的人打死在家中。我认为武装起义不好的、不理智的,并谈了一些理由。那个皮肤稍黑的笑了一下,语气平静地说:“我们不这样认为。”我接着说起杀人是一种罪恶,谈到上帝,他俩互相看了一下,那个黑眼睛耸了耸肩说:“那么按照上帝的法规,我们无产者就应该让人剥削吗?以前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觉醒了,不再……”我给他们拿了一些小册子,大都是宗教方面的,他们看了看标题,显得不太满意。我说:“也许你们不喜欢,那就不要拿去了。”那个皮肤稍黑的说:“为什么不拿?”同时把这些小册子塞进怀中,然后他俩向我告辞。
尽管我没有看报,从家里人的谈话、接收的信件和来访者的议论中,我对近来国内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特别是知道老百姓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只有一部分人谴责政府,现在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指责政府的行为是非法的、有罪的,风潮的产生其根源在政府。持这种看法的有教授、邮政官员、作家、小店主、工人甚至警察。国家杜马被解散后,人们的激愤愈加强烈,最近频发的政府杀人事件使得这种激愤达到顶点。我知道这些情况,而跟这两个人的谈话就像一种力量,使逐渐凝固的水突然变成了冰,我以前获得的这些印象突然变成清晰无误的信念。
跟他们谈话后我清楚了:政府为打压革命而采取的种种罪恶行径,不但不能把革命打压下去,反而让它愈演愈烈。我清楚了:即使革命烈火由于政府的恐怖镇压而暂时熄灭,它也不会真正消亡,只不过是潜藏着,以后会以给更大的能力爆发出来。我清楚了: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只要碰上易燃物一点就着。我清楚了:政府只有停止所有的镇压活动,不仅停止死刑和抓捕活动,还要停止流放、迫害和查禁活动,才有可能缓解民众的愤慨。我认为,现在政府能够做的就是向革命者妥协,允许他们按找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也知道,如果我提出这样的建议,只会被人看作疯子。因此,尽管我知道,政府继续这样干下去,只会让局面越来越坏,而不会有丝毫改善,我却不能把这一点写出来,也不准备把它讲出来。过了快一个月,我对时局的估计不幸被言中了:死刑、屠杀和抢掠越来越严重。我从人们的谈话中和随便翻翻的报纸上可以知道这一点;我还知道民众对政府的敌对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前天我散步时,一架马车与我顺向而行,到我身边时,车上跳下一个年轻人,来到我面前。他个子不高,留着一撮淡灰色的胡子,看起来很有灵气,但目光不友好,似乎有些忧郁,脸色也不太健康。他身穿一件皮夹克,有些破旧,脚穿一双高腰皮靴,头戴一顶带盔头的蓝帽子,人们说这是最时髦的革命服。他向我要一些小册子,我看出这是他想同我搭讪的借口。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就住在附近这个村子里,是农民。前不久村子里有一些妇女来找过我,她们的丈夫被关进监狱。我对这个村子很熟,曾带着官方出版的识字课本来到这个村子,这些农民身体健美,很有灵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我办的学校里,那些学得好的学生大都来自这个村。
我问这个年轻人,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农民的情况。他以一种十分肯定的态度说:这一切都要归咎于政府;这些农民都是毫无缘由地被抓进去的,先是遭到残酷的殴打,浑身是伤,然后被关进监狱。我问他,这些农民被定的什么罪;他说了半天我才听明白,他们聚集群众,发表演讲,大讲没收土地的必要。我表示,要实现所有人平等占有土地的权利,只能让土地不再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但不能采用土地国有以及其它强制性的方法。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为什么?只要组织起来就可以。”我问:“怎样组织?”他说:“到时候就知道了。”我问:“你说的是武装起义吗?”他回答:“这是必然的,尽管很可悲。”
我给他讲了一些道理,是最近我经常讲的,即不能用恶来战胜恶;只有通过不参加暴力才可能战胜它。他看了看我,皱着眉头说:“但人们已经活不下去了:没有工作,没有土地,出路在哪儿?”我说:“我不想跟你争论,从年龄上讲,我可以做你爷爷了。我只想告诉你一点,年轻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不对的,那么你们的行为也同样不对。年轻人,要好好生活,不犯罪,不违犯上帝的法规。”他表示不满地摇摇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一万个人就有一万个上帝。”我说:“无论怎样,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再干下去。”他回答:“那到底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忍受下去吧?到底怎么办?”我感到这个谈话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想离开,但他叫住了我:“你可以为我订一份报纸吗?”我拒绝了这个要求,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他。这人就是本村种地的农民,还不是失业的手艺人;而现在有数以万计的手艺人无事可做,在全国各地流浪。
回到家中,我 发现家里人也跟我一样心情沉重。他们刚刚看过新来的报纸(这是10月6日)。女儿告诉我:“今天又有22个人被处死,这太骇人听闻了。”我说:“这不仅是骇人听闻,简直是荒谬到极点。他们的倒行逆施越来越厉害了。”有谁接我的话说:“那么到底怎么办?总不能让这些杀人的、抢劫的就这样算了。”这样的话我已经听过多次。那两个从果园来的流浪汉和今天遇到的那个农民都对我说:“到底怎么办?”
有一种人,即革命者说:“我们不能就这么忍受这个无德政府的疯狂暴行,它祸国殃民,为害极大。我们也并不满意自己的做法,但到底怎么办?”还有一种人,即保皇分子说:“决不能让那些组织动乱的人夺取权力,决不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管理、破坏和毁掉俄罗斯。现在我们采取的做法是严厉了一点,但到底怎么办呢?”这样,我想起跟我接触的革命党和保皇分子,包括今天的那个农民,还有那些制造炸弹、杀人抢劫的革命党以及那些成立军事法庭、枪杀和吊死人的人,他们都是走上歧途的不幸者。这两种人都认为自己做得对,同时又问道:“到底怎么办?”
他们都问:“到底怎么办?”然而这问话的意思并不是“我应该怎么办”,而是说“如果我不这么办,那么情况会更糟”。我想对他们说,如果你真是把这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而不是为自己辩护,那么它的答案十分简单:你不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沙皇、部长、士兵,或者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应该仅仅把自己看成一个按照本性去行事的人,也就是遵循将你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力量之要求去行事,遵循上帝的要求去行事。这样一来,所有的罪恶都可以消除,人们有如拨开云雾见青天,因为以前他们都以为只有自己是出类拔萃的人,可以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其实是给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普遍规则,是有理性的人所公认的,并被各个民族的传奇、宗教、科学和人们的良心所证实。这一规则是:为了实现人类的使命和幸福,所有的人都应该互相帮助和关爱,最起码不应该有意侵犯他人的自由、杀害他人的生命。然而现在人们却分为不同的派别:有些是皇帝、部长、士兵;另一些是各种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进入这种种角色后,忘乎所以,以为违犯原先的普遍规则反而可以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幸福。但我相信,目前深受其害的大多数人最终会识破这种骗局,从而摆脱暴力和犯罪。我们应该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按照上帝的要求去行事。一个没有完全丧失良心的人,一旦抛开自己的社会地位,无论是部长、警察还是某个委员会的成员,都会意识到上帝的这一要求。这样一来,我们的悲惨命运就会改变,种种灾难就可避免,俄罗斯大地就会成为天国。
即使现在只有一部分人这样去做,以后人会越来越多,而这个世界的罪恶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离所期盼的天国也就越来越近。
——到底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