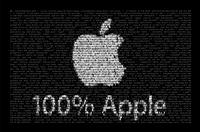2008年6月20日,中国发展简报邀请在川当地以及陕甘黔的NGO就“5·12地震”期间参与赈灾的机构行动和联合在四川科技大会堂举行了小型的现场交流会。与会的40多家NGO纷纷发言并与在座的同行进行了交流和分享。现将当天与会的各方机构发言进行编辑整理,摘录其中部分发言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救援联合的评价与反
思
地震发生后,在四川迅速成立了两个NGO联合办公室。四川NGO救灾联合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张国远,办公地点临时设在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另一个是四川社会科学院郭虹领衔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在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办公。来川救灾的民间组织,大部分都与这两个办公室有过联系。所以会议一开始,郭虹和张国远就联合情况做了简单回顾,也提出了遇到的问题和合作中的困难。
四川社会科学院郭虹:5月15日,四川NGO联合搭建了一个平台。既有信息的交流,也是志愿者的一种组合,志愿者与机构之间的对接。在这个舞 台上,四川NGO集体亮相。5•12办公室的宗旨是,“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 有序参与 有效服务”。前两句是国家在这次汶川救灾中针对全国、中国民族的 口号,后两句体现NGO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我们的共同参与。这种参与,是通过大家的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而达成一种有效合作。其中除 了理念的一致,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操作,比如及时建立一些相应的规章制度,一种议事的机制。这种有效参与,第一是对灾区人民,此外,还针对一些特别群体,比如为灾区的妇女、儿童、艾滋病患者或HIV感染者以及包括各种没有第一时间被关注到的社会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四川NGO救灾联合办公室张国远:地震发生后,NGO聚集到一起讨论做点事情。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做紧急物资的募集和发放,另外一个是做倡导。后来,我们这几家NGO倾向第一种意见。14号在根与芽的办公室临时成立了。在同一使命驱动下,大家很快开始行动。我们开了一个小会,根据每个机构各自特长分工,当时我负责募集资源,包括现金和物资;罗丹负责物资进出,贵州行动组负责前方的需求调查,后来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的邢陌也加入进来,负责仓库和物资转运。后来,麦田计划的“水瓶”成为我们办公室的专业会计。联合办公室当初成立的时候达成的共识,就是紧急援助。在紧急援助结束后,我们就会自行解散。所以,5月30号我们办公室就在收尾工作,按照之前协商的解散程序在做一些事情。到了6月初,办公室就通过网络或其他渠道发布我们的整个财务收支状况以及一些工作情况,然后办公室就正式解散了。
目前反思主要是:联合办公室内部沟通不够,与整个发起成立的网络成员沟通不够;联合办公室没有制定一个成文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也没有一个成文的行动守则,大家可能都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在行动,没有一个有框架的行动准则。
另外,联合办公室还有两个问题:一是警方调查。我觉得联合办公室是一个没有注册的、临时的 一个机构,它的资金都是过我的私人账户。其实被 警方调查也是比较正常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任 何问题。我们反而觉得这样的调查对我们的公信力有所提升。
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以攀枝花东区志愿者协会的名义参与了很多救援行动,这个行动属于重大活动,但没有按照攀枝花民政局的要求,向当地的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申报,所以我们东区承受市政府很大压力。此外,这个款项是经过我个人的账户,也没有给政府带来比较好的影响。所以迫于压力,我辞去了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的职务,现在任攀枝花社区发展研究主任。我打算用两三年的时间继续从事灾后重建工作,目前,这个项目小组叫NGO 备灾中心,是在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下的机构。
与政府的关
系
救灾除了需要NGO之间的合作,另一个重要合作对象就是政府。在这方面,参与救援机构在一个多月里有了各种经历和经验。
陕西妇女研究会高小贤:像我们这种本土NGO在资源动员方面不足,遇上紧急情况时申请资金还 是有很多的困难。而且能力和资金并不匹配,往往有能力的没资金,有资金的并不一定能找到有经验的人。
NGO在四川赈灾过程中的空间是靠我们主动争取的,而不是靠政府邀请的,这还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这个博弈要靠NGO主动,提供更好的、专业化 的、能够被政府所采纳的服务,也可以和政府讨论一些专业性的理念。做好了,就会让政府看到NGO 的长项,这可能也需要NGO的联手。
四川圣爱特殊儿童援助基金会孟长寿:圣爱背景相当特殊,既是NGO机构的成员,也是基督教会成员,又是基金会和红十字会的会员。我们这次就是以红十字会员身份参加救灾。
我们手上有两张表格,一张是受灾地区学校调查表,一张是受灾地区官方调查表。我们把两张表合起来研究之后,才确定在哪里办学校。在发放物资方面,我们也很谨慎。最难的就是让政府认可、接纳我们,不管是NGO也好,教会也好。我们在绵竹设立了一个儿童(心理)辅导站,当时我们不要媒体进行采访和报道,不许任何的干扰,怕给受灾儿童更深的伤害。但四川当地有关部门说我们不进行宣传,是因为我们在传法轮功,坚决把我们赶走。
梁漱溟乡建中心何志雄:14号我们组织队伍,统一着装就过来,带着工具和物资。这样会很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信任。(物资)发放我们是要和政府协调的,否则会出现发放不均,毕竟政府 熟悉那里的情况。
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办陈太勇:最初的参与,我们是以救援为主,同时评估需求。救援物资到位 之后,一定要和当地政府协调之后进行物资分发。我们尝试了多种渠道,最好的还是到基层,要和乡镇政府一起进行,否则会造成物资分配不平均。还有就是与国内外NGO组织的合作。这次救援对于我们是第一次尝试。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田军:我们有一个经验,不管机构合不合法,也主动向领导汇报。不管组织 接不接受,我们也要每天汇报我们的工作状况。这样便于增加民间组织救援工作的透明度。
5•12平台想做调查研究、情况反映、决策建议,但我们也希望大家提的建议是通过成都科技协会这个平台。有一个问题是,政府都想在短时间内做到第一名,这个(与重建的长期性)冲突是很大的。安排一些大的国企要做形象工程,这种形式就 给NGO的空间很小,我们要和政府沟通。
农家女发展中心谢丽华:第一点是,我们真的应该沉下心来做事。第二点,对接要把自己的专业背景应该充分地发挥,或是更加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建设,把专业做得更专业。不能是 NGO撤离时,还是把问题留给了政府,自己却拿着资料研究去了,最后留下做事的还是政府。
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吴登明: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协助政府、支持政府,我们不能代表政府。这个位置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要搞调查研究,把一 些相关的建议和专业的东西,像住房怎么安置提供给政府。在重建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灾民的意见。如在三峡的建设上,虽然我们移民很多,房子也建得很好,但村民不满意。这就是没有尊重当地村民的意原。
重建需要专业与专
心
成都爱白青年中心雷刚:地震后,经过我们的商量,物资和捐款是没办法做的。所以,我们把目标锁定在最擅长的心理援助。包括对灾民和学校 的紧急心理干预和援助。工作主要是在网上进行心 理辅导,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从网上到网下的。同时,很多机构想通过当地的一些组织对接而进行活动时,我们就帮助这些机构找到他们能够对接的组 织。此外,有什么样的策略也很重要,我们发布的信息和招募的信息,国内有十多个电台,包括电台,还有媒体,帮助我们宣传。
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黄磊: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灾后重建和现在还没有结束的救助中,更多的考虑参与重建过程中应该有长期性、环保生态的 一个观念。过渡房造成的二度污染是非常严重的,以后泡沫、锈住的钢板会给当地造成很大的麻烦。还有重建可持续性和当地资源的联系也很重要。此 外,可以帮助当地的灾民参与到重建的过程中来,给他们提供工作的机会,给他们建造自我价值认同感。
我觉得我们的服务应该重服务、重专业。更重要的是,我们带着爱心,带着资源进来,要陪伴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现在招募的是3年到5年 的长期的志愿者,陪伴他们度过这段时间。因为短 期的陪伴,很容易造成二次损伤,尤其是孩子。
陈太勇:我们的优势是社区生计项目,就是帮助社区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帮助增强社区凝聚力。挑战有两个:第一个是受灾面积大,要选择项 目点比较困难。第二个如何整合机构内外的人力资 源和响应能力,实施历来最大的灾后重建和救助发展项目。
绿色江河杨欣:作为NGO,确实比较弱小,但在每个领域都有我们的点,大家不要在一个领域,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做出自己的特色。只 有做出一个合格的高质量的产品,这样才能在做下 一个产品的时候获得更多的支持。
另外,我们要多做调查,包括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因为灾区比较大,我们只能进入像成都这样交通比较方便地地区,其实生物多样性还没有打开,打开之后肯定有很多NGO施展的空间。
何志雄: 关注政府灾后重建政策非常重要。政府会考虑的很多。我们要跟着政府走的话,会方便我们了解怎么样使用更好的方式进行建设和帮助,也会减少我们和当地政府和政策的矛盾。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志愿者要在点上长期跟着,后期的物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农村调查了好多个村,有一个很严重的、对NGO直接挑战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回应。村民的房子已经损害的非常严重,但他们对一些非政府 组织不是很信赖,他们认为能够为他们建房子的只有政府。他只是认为你过来关心他,以表现你的爱意,但并没有指望你把房子建起来。这个问题是最令人焦虑的。如果NGO要下去的话,怎么回应他们的这种需求?
我们在的那个社区,不建议建生态房。农村住房的规划,另一个问题随之产生,就是说规划还不清楚。那么群众协作的建房在目前阶段就不具可操作。我现在所在的都江堰,是成都市整个规划局在 做下一阶段的农村永久性住房的规划,包括一些政策、选址等问题,需要时间,需要协调。
田军:当初我们也想继续在灾区做,但是牵涉到一个规划的问题,在都江堰和彭州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也给政府提建议,说不要与自然强度对抗。硬要弄一个规定新建房必须是八级九级抗震的房子,其实是不经济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倡议:资源共享、网络建
设
这次参与地震救援的大部分机构没有经验,所以未来的重建中无论是行动者还是专家,都对信息与资源共享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各个机构通过专业的力量联合起来,推动灾后的重建。
梁漱溟乡建中心曾利华:5•12平台应该主动一点,在相同的领域,和以前比较成功的团队取得联系,把信息公开。资源整合这种意识应该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杨团:这次大震,也震出了一个大机会,使整个中国人文价值的重建,通过大震震出来的,一个是NGO的崛起,一个是 NGO的联合。不管是基金会还是草根组织,能够结合起来发出一种集体的力量,就像这次全中国13亿人民的力量一样,可能是一种最大的收获。
台湾的专业人士做NGO的非常多,很多教授都是在做NGO的执行长。他们把很多专业知识专业能力都带进来。我们大量的NGO是不在地的,真正在地的包括在四川的,在灾区的几乎没有。而台湾在地震当地本身就有许多的NGO。我们怎么样扬长避短,唯一的办法就是联合。如果动员村民站起来,能够让灾区群众有公民意识这个是很重要的。
台湾在灾后七天就有了NGO的联合,15天到1 个月期间这种联合就基本完善,921基金会作为他的后身,到今天还在运作。整个抗震维持了九年。这种组织不是登记注册的,而是应号召而来的,过两年自己向社会宣布解散。
我们NGO规模比较小,没有一个联合的基础,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大联合与小联合的结合。小联合是指,比如说有一个项目,怎样去包它,怎样和上面的基金会去谈,一家是不行的,你的能力、专业,人力都不够。
根据不同的议题组成工作团队,这样就能把 NGO的各种能量调动起来,大家的积极性是非常可贵的,但这能维持多久,重要的就是联合协调的 机制和组织。台湾的经验是:我们没有公权力,但是我们有公信力。所谓公权力,是他们没有注册,他们形成了一个全盟(全称“全国民间灾后重建联盟”),主要任务就是工作协调和捐款监督。
阳光医生张丽坪: 如果可以,做一个灾后NGO网络,与社会媒体和专业媒体做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这要落实到每一个机构,因为做网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很多后台和前台的维护。如果本土的一个机构愿意承担这个工作还是可以的。
我们了解到很多组织接到很多赈灾资金,但很大一部分并不知道该怎么用。NGO应该合力证明我们可以做的好,可以很好的分担使用这个资金。
多背一公斤小v:我们怎样在一个法律空间下做这个事情。财务审计和法律是草根NGO共同面对的问题,还有政府的策略,很多地方策略都是不同的,怎样实现这样的信息和资源的共享。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像刚刚讨论的生态卫生间的建设,这个是完全可以模块化的东西,我们怎样把这个资源共享。很多组织都有自己的特点,但面对大家都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样把它模块化,怎样资源共享化,怎么把它解决掉。
杨团:我强有力主张单一窗口。政府也单一窗口,否则我们的力量聚集不了。怎么能做到?我们认为政府的单一窗口力度不够,但也努力在做,NGO显然是分散的,分散也有非常大的好处,不分散也没有办法覆盖,但真的想把整个的NGO联合意识提升,那就得考虑主张单一窗口。
(此由王辉、刘海英根据会议录音编辑,未经发言人审阅)